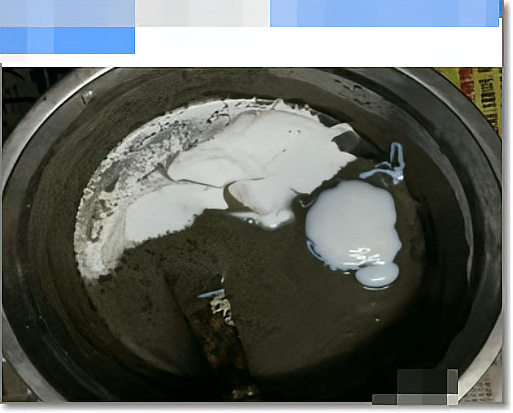“读什么”与“怎么读”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诵读作为阅读教学文本解读的方法,旦橡即“怎么读”,现在名目繁多,如:吟读、朗读、朗诵;范读、仿读、跟读;齐读、单读、自由读、分角色读;析读、品读、评读、研读;等等。这些读法类型的视角各异,从声音表现、组织形式到阅读层级等均有涉及。本文择取的是与诵读目的和对象相关的诵读方法。诵读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文本的阅读目的,与此相关的“怎么读”是指读什么,即从何处去理解感悟文本,走进文本世界;诵读方法作用的对象是特定的文本,“怎么读”是指以何种声音表现风格、把握基调。 诵读方法是否恰当,首先当然是审核诵读作为一种阅读的方法对于特定的这一个文本是否适宜。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提到,“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显然,在曾国藩眼里,要达到“得其雄伟之概”、“探其深远之韵”的阅读目的,诵读是阅读《四书》等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最为恰当的方法。本文则是在文本适宜采用诵读法的前提下,探讨诵读方法的具体内容,以及与阅读目的、诵读对象的契合性。一王荣生先生认为,“怎么读的问题,就是在具体的文本中去读什么地方、在这些地方读出什么的问题”。诵读作为阅读的一种方法,首要的问题也正是要明确:读什么?从何处走进文本?从何处读出什么? 实际上,若已确定采用诵读作为解读文本的方法,阅读目的也已受制于方法所能达成的一般的目的了,也就是“诵读什么”中已隐喊隐含着能“读出什么”。从理论上说,感知塑造言语声音形态这一过程有两个终点:一是理解感悟文本的意义情感;二是形成感知言语声音形态的能力。前者是一般所谓的把握文本内容,从声音走向了意义与情感;后者是所谓欣赏与表现文本言语声音的能力,关注言语声音本身,培养对言语声音的敏感。我们以为,既然诵读是当下文本阅读所适宜的方法,那么阅读目的是没有理由抛开上述终点的。问题是,方法所隐含的目的如何在特定文本阅读目的中具有意义?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这里的视角是:课程目标属于语言教育还是文学教育?王尚文先生近来提出了语文课程的复合性话题,他认为语文课程可一分为二为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语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所养成的主要是语言素养;文学教育虽然也是从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出发,但其终点是感受、感知、感悟人的生命体验,最终认识自己,理解自己,所养成的主要是文学素养。由此来看,归属于文学教育的文本,阅读目的可以单一地指向内容。而归属于语言教育的文本,其阅读目的中一般包括了两个方面,分别指向文本内容和语言表现力,显然这里的“语言表现力”也包括文本言语声音形态的表现力。所以,语言教育中的诵读,是走进文本意义情感世界的桥梁,是咬文嚼字的手段,有时又是体味言语声音形态自身魅力的途径。 这样,从语言教育的角度来教学《声声慢》,要把读什么——感知舌音、齿音和入声韵、叠音词,具体化为理解体悟压抑凄婉的情感和体味音韵节律的表现力。教学实践中早已进行着这样的诵读:对诗词韵文中语音修辞的品读;从不同语调的比较中体会句式的流转顺畅,如“仕宦至将相,锦衣归故乡”与“仕宦而至将相,锦衣而归故乡”,等等。显然,这样的读法并非归属文学教育的文本所必需,因为文学教育可以得意忘言。 放任自主诵读体味,学生能读出什么很可能是一笔糊涂账。明确文本阅读目标的归属,确定文本阅读目的,研究文本言语声音形态的特点,明了“在何处读”、“读什么”,设计引导学生从中“读出什么”的路径来。——这些方面,教师应该有积极的作为。二基于声音表现风格的“怎么读”,是为了把握文本语调、节奏的诵读基调,其恰当模渗旁与否和诵读对象——特定文本的文体特点相关。曾国藩所言《四书》等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密咏恬吟”不可,表达的就是这两者间的关系。实践中所要探讨的是诸如哪一首(类)诗适合“高声朗诵”,哪一篇(类)文宜于“密咏恬吟”这样具体的问题。 对此,前人已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对今天的研讨很有启发。黄仲苏先生在其《朗诵法》中“审辨文体,并依据《说文》字义及个人经验”确立了四大类“朗诵腔调”: 一曰诵读。诵谓读之而有音节者,宜用于读散文。如四书、诸子、《左传》、四史以及专家文集中之议、论、说、辨、序、跋、传记、表奏、书札等等。 二曰吟读。吟,呻也,哦也。宜用于读绝句、律诗、词曲及其他短篇抒情韵文如诔、歌之类。 三曰咏读。咏者,歌也,亦作永。宜用于读长篇韵文,如骈赋、古体诗之类。 四曰讲读。讲者,说也,谭也;说乃说话之“说”,谭则谓对话。宜用于读语体文。(朱自清《朱自清论语文教育》,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朱自清先生在最初刊于1942年的《论朗读》一文中,把黄仲苏先生的四类归为三类:诵、吟(吟读、咏读合并)、讲读(分为“读”与“说”);并说“文宜吟诵”,“语只宜读或说”(后来他改变了这个观点,见下文),依据主要是语言是否自然。 朱自清先生较为细致地探讨了“讲读”法的要求及其适用性。他认为,“讲读”分为“读”与“说”。读,要舒缓不迫,字字分明,注重意义,注重清楚,虽也有抑扬顿挫,但不显著,整个效果是郑重和平静。说,是如赵元任先生所言“照最自然最达意表情的语调的抑扬顿挫”来表达。他认为黄仲苏的“讲读”只当得他的“说”类。读,适合绝大多数的白话诗文,和“一切应用的文言”。如宣读诏书、判词、公约、守则等就是典型的“读”,所举具体的文本是《总理遗嘱》。说,适宜少数用口语调写成的白话诗文。所举大多是具体的文本,如:老舍的《一天》,朱自清的《给亡妇》,康白情的《一封未写完的信》,徐志摩的“无韵体”诗,丁西林、曹禺的戏剧,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前几章等。(朱自清《朱自清论语文教育》,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在写于1947年的《论诵读》一文中,他使用了“诵读”一词,从声音表现的风格来说,是“讲读”法的延续。他认为,诵读是“多少要比说话做作一些”的“说话的调子”。诵读第一要口齿清楚,吐字分明,字字清朗,这与“读”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对读法的选择,他已不再单一地依凭语言是否自然,而是结合了阅读目的来论。他认为,“在了解和欣赏意义上,吟唱是不如诵读的”,“所以就是文言,也还该以说话调的诵读为主”。(朱自清《朱自清论语文教育》,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结论,还有策略与方法。我们需要像他那样来探讨问题,以文本语言的视角来研究特定文本的“怎么读”。有关朗读技能养成的一些训练体系设有按狭义的文体(仅指体裁)训练的篇章,意谓一定的技能与一定的体裁相应,但实际的训练还是得面对特定的文本展开。文本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种技能训练并不能满足特定文本的诵读需要,因为同一体裁并不意味着语体、风格的一致。如现代诗,有适合朗诵的,有适宜“读”的,也有如朱自清所言宜于“说”的。 从体裁来确定基于声音表现风格的“怎么读”并没有抓住关键。文体包括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面。对于特定的文本来说,与“怎么读”最为关切的是语体。语体,即语言的体式。一般地说,一个文本的语体是一个复合体,一种是体裁所要求的规范语体,如与章表奏议匹配的是典雅语体,而赋颂歌诗则必须选择清丽的语体;另一种是作者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所选择的自由语体,这完全是作者的创造,是文本语体更为重要的方面,它使文本获得了独特的语调和语势。这种属于作者个人的自由语体品格稳定地发挥到一种极致,并与作品的其他因素有机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风格。我们可以这样说,主要的是作者自由创造的语体决定着特定文本的“怎么读”。 实际上,体裁作为文体的一个范畴也从语体中表现出来了,但在文体发展极为丰富而理论相对滞后的今天,“怎么读”若基于体裁所表现的语体,连能否把握基本语调也是很成问题的。如目前国内流行把文学体裁分为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和散文四类,而散文是语文教学的主导文类(王荣生),在这样的语境中,“怎么读”很多时候是根本无法基于体裁的。如《现代语文》读本有一个名为“风格: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单元,所选多为散文,分为“朴素”、“华丽”、“雄浑”、“柔婉”、“洗练”、“绵密”六个部分,实际上就是从自由语体的角度所作的归类,这些散文“怎么读”只有基于自由语体才能够准确地把握。(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博士生;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