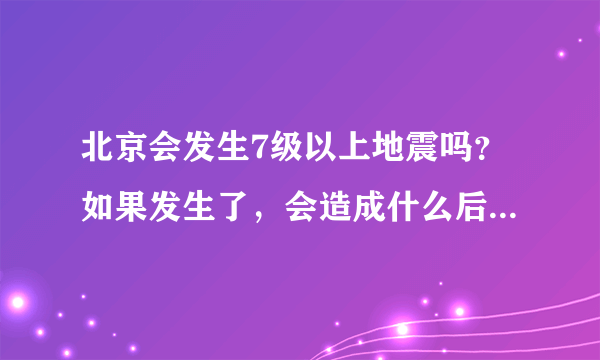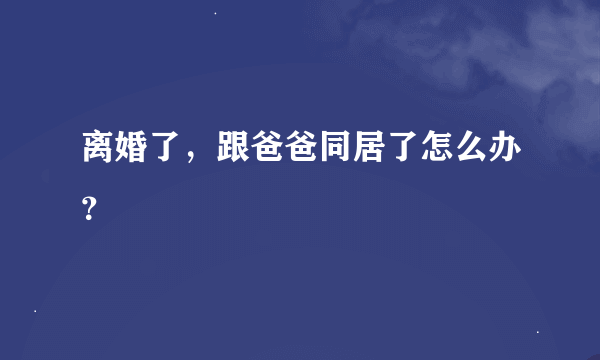什么是西昆体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内容提要 西昆体诗虽孕育于宋初馆阁唱和之风,但不能说是贵族文学,其代表人物杨亿风骨清亮,具有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显示了宋代士人典型的气质人品;西昆体与白体,不仅对立,而且相互渗透、并行发展,故它实际上是白体、义山体、唐彦谦体混合的产物,一方面重视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符合宋代文化的内转趋势,另一方面使白诗和晚唐诗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唱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本文重点论证了杨亿咏史诗的规讽之意,以及他的咏物、咏怀诗中的个人感怀,认为可称盛世哀音。 西昆体不仅仅是对晚唐诗风的简?quot;复归",它为真正的"宋调"的成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杨亿 西昆体 宋诗 再认识 对宋初曾盛行于诗坛的西昆体,建国以后的各种文学史论著几乎是全加否定。新时期以来,始有论者不断提出异议 ,从思想和艺术等方面肯定了西昆体、尤其是杨亿诗的价值,十分有说服力。但是,几种较有影响的文学史及宋代文学的著作,在论及西昆体及杨亿诗时,尽管已注意拨乱反正,但仍认为:"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这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相容",并说"西昆体有明显的娱乐倾向","所以主张变革文风的人首先要对付它" ;"足见他们的创作目的仍与宋初承袭元和体的风气相同,是为了唱和消遣",杨亿只有在担任地方官时所作及学习白体的诗歌(即在《西昆酬唱集》之外的作品)才是"内容充实的作品" 。几种较晚出的论著,一方面吸收了学术界的新成果,对西昆体作出了较全面的评价,但所下的结论则是:"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乏的,它们与时代、社会没有密切的关系,也很少抒写诗人的真情实感","尽管西昆体的成就高于白体和晚唐体,但它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袭",或云"只是它的主流并未向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的形成方向迈进,反倒实现了又一派晚唐诗风的又一次复归?quot; 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述未免失之粗廓。这里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西昆体诗是贵族文学吗?第二,西昆体与白体只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吗?第三,西昆诗风是否只体现了唱和消遣拆毕的娱乐倾向?本文试图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杨亿及西昆体的认识和评价再作申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为什么会提出西昆体是贵族文学呢?大概因其发生流播于馆阁的缘故。宋初五十年左右流行白体诗,皆盛行于宫闱馆阁,或为君臣之间御制奉和,或为臣僚之间酬答唱和。自真宗朝起,同样产生于馆阁词臣唱和的西昆体逐渐取游镇而代之。从表面看,白体与西昆体都是宋初宫廷唱和之风的产物,其实未可一概而论。 馆阁之称,本承五代,梁迁都以汴,始设昭文、集贤、史馆,谓之"三馆",宋太宗太平兴国中,合三馆赐名崇文院;端拱中,始分三馆,藏书万余卷,别为秘阁,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 馆阁文人实为宋初最早的文学群体,习作馆阁体诗文,也表现出宋人具有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可能有鉴于此,北宋吴处厚总结宋初诗文创作时提出,文有"朝廷馆阁之文"和"山林草野之文"的区分。其论前者云:"朝廷馆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杨大年、宋宣献、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诏,皆婉美淳厚,过于前世燕、许、常、杨远甚,而其为人,亦各类其文章?quot;(《青箱杂记》卷五)所列代表人物之首即为杨亿。同书还说,同是真宗时人的夏竦,曾以文章谒翰林学士盛度,盛度赞曰:"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直至神宗时,任职秘阁的王安国还说:"文章格调,须是官样。"此所谓"官样",亦即馆阁气。宋初馆阁体流行,若按吴处厚的说法,宋初三体中,白体、西昆体显属馆阁之诗,晚唐体应属山林之诗。 那么,馆阁文人作为宫廷诗苑的核心和主力,是否其人及作品一定具有贵族趣味呢?窃以为不可一概而论,须作具体分析。 宋初白体的代表作家,主要是五代旧臣,新朝宰辅。徐铉仕南唐,任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入宋后官至右散骑常侍、左常侍;李昉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入宋后位极人臣。李昉、苏易简酬唱之《禁林宴会集》,李昉、徐铉与其他馆阁词臣的《翰林酬唱集》,首开宋太宗时馆阁酬唱之风,同为真宗时宰辅大臣的李至、吕端,也是白体诗的倡导者,李昉、李至有《二李唱和集》传世。宫廷流行的白体诗确是代表着当时诗歌创作的贵族化倾向,这是因为,一,宋初文臣身居高位,安享尊荣,滋长了旅磨芹乐天安命、知足保和的思想,因官高禄厚而踌躇满志,其生平思想行事,与白乐天晚年颇为接近。白居易归休后居洛阳履道里,与年高而不事事者九人燕集,绘《九老图》,是诗坛佳话,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九说:"至本朝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慕乐天之为,得宋琪等八人,年七十余,将为九老会,未果而卒。"可见李昉等人的人生旨趣;二,宋初大臣多以文士入宰辅,本因文章诗赋成名,故声应气求,欲借相互唱和标榜清雅,自抬身价,白乐天诗风(即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所说的"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与"杯酒光景之小碎篇章")之内容体制与宋初文臣之身份及生活作风最为相宜,故趋之若鹜。《二李唱和集》李昉序云:"朝谒之暇,颇得自适,而篇章和答,仅无虚日。……昔乐天、梦得有《刘白唱和集》流布海内,为不朽之盛事。今之此诗,安知异日不为人之传写乎?quot;我们从此集中诗题,如《蓬阁多余暇》、《秘阁清虚地》、《自喜身无事》等,可见其志得意满的心态。当然,白体能流行,君王之提倡,得语之容易,也是重要原因。 再看西昆体作家,本因《西昆酬唱集》得名,其酬唱活动在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三年间,即编《历代君臣事迹》的初期。参与编书的馆阁词臣并未加入酬唱活动,加入酬唱的17人中,有多人又未参与编书,有的根本未在馆阁任职,故既是馆阁词臣、又是《西昆集》作者的,主要是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 ,这三人中,钱惟演的身份较为特殊,杨亿、刘筠近似,但其身份地位与宋初白体代表人物显然不同。两人均以科举入仕,是宋代新进学士;而同为馆阁新进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善于趋附,人格卑下,杨亿则异于是。真宗后期,为群小包围,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希上邀宠,杨亿侧于其间,遭到排挤,处境艰危。但他为人正直,风骨铮铮,不愿苟且自辱其身。其身份虽为文学侍从之臣,但为人立志甚高,自谓"史笔是非空自许,世情真伪复谁知" (《读史学白体》,《武夷新集》卷四)。时人或称其"性特刚劲寡合"( 欧阳修《归田录》),或赞其?quot;忠清鲠亮之士"( 苏轼《议学校贡举状》),显然杨亿并非谀君阿世之徒。 关于杨亿的人品节操,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有《杨文公论》一篇(《鲒崎亭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本),盛赞杨亿风节,久被研究者所忽视,兹移录于下: 真庙一代,名臣多矣,乃以寇莱公之雄视一时,独拳拳欲引杨文公以共事。予初谓文公乃词章之士,何以得比于莱公?及反复其遗事,而后知文公之劲节,鲜有其伦。文公当日回翔馆阁之间,最受当宁宠眷,而卒不登二府,盖其百折不回,岸然自立,故群小竭力以排之也。真宗时之群小,莫如王钦若、丁谓。文公尝与钦若同修《册府元龟》,每至馆中,未尝接席而坐;钦若去朝,百官皆以诗送,文公独无有;钦若请之真庙,传宣索诗,而文公竟不作。谓亦遣人求婚,拒之甚峻,可谓浩然之气,直养而无害者已。故其大者,如当草明肃后诏,而力辞之曰"如此富贵不愿也";其小者,如草制偶遭"粪壤"之诮,而即辞官。 盖宋初词臣,前之如王学士元之(禹偁),同时如刘学士子仪(筠),皆以风节自见,而文公尤为铮铮。乃若澶渊之役,百寮震慑,而莱公独与文公饮博自如,其所养有素矣。 朱子乃讥其溺于释氏,故当莱公被祸之时,宣召文公至省,便液污地,以为未尝闻道之戒,是何其言之过欤!文公之佞佛,特其学术之疵,而不害其风节;至于便液污地之说,此当日小人谤之。"五鬼"之恶,不过贝锦,株连之祸,不过渡海,其视澶渊危急为何如也?且以文公之倔强,其可以得罪者多矣,前此之风节何如,谓其垂老而丧之,百炼之钢,忽成绕指,无是理也。东坡谓:"人之所恃者气,正气所恃,非威武所能屈。故因太白之不礼高力士,而知其必见胁于永王,且信其为王佐之才。"可谓善论人者,吾于文公亦云。 此文中所述杨亿失宠诸事,史书皆有记载: "草制偶遭'粪壤'之诮",指大中祥符六年六月,杨亿草答契丹书,有"邻壤交欢"语,真宗阅后,在文稿上注"朽壤"、"鼠壤"、"粪壤"等字嘲笑之,杨亿即以不称职求罢,真宗谓辅臣曰:"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并见范镇《东斋纪事》、欧阳修《归田录》)"草明肃太后诏",指议册刘皇后,真宗欲由杨亿草制,使丁谓传旨,杨亿不愿,丁谓云:"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杨亿答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真宗无奈,乃命其他学士草之。(同上,并见孔平仲《谈苑》)"钦若去官"拒送诗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据江休复《杂志》,记杨亿与王钦若有隙:"亿在馆中,钦若或继至,必避出,他所亦然。及钦若出知杭州,举朝皆有诗,独亿不作。钦若辞日具奏,诏谕亿令作诗,竟迁延不送?quot;此事孔平仲《谈苑》亦载。又《东山谈苑》云:"杨亿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入其党。因间语亿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刚。'亿正色厉声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 又如对待真宗封禅,杨亿虽曾参与详定封禅仪注,其态度与诸大臣显然不同。王钦若、丁谓等佞臣在东封西祀事件中纷纷撰作颂、记,什么《大中祥符封禅记》、《社首坛颂》、《太山铭赞》、《封祀坛颂》等,因吹捧而得封赏,甚至连颇有识见的王旦都未能免;身为文臣的杨亿,却始终持保留态度,也未留下颂赞文字。如此坚持自己的"气性",遇事"不通商量",必然要引起真宗的疑忌和不满。 如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载:"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以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藁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谮矣。"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亦云:"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后苑,宣示御制《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皆新制也,笑谓近臣曰:'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语盖旨在杨大年也。" 杨亿所作《受诏修书述怀三十韵》诗冠于《西昆酬唱集》之首,其所述情怀,并无优游岁月、富贵得意之态,相反,"危心惟觳觫,直道忍蘧蒢"云云,适可见其临深履薄、动辄得咎的危机心理。所以可以说,与宋初馆阁宰辅大臣徐铉、李昉、李至、吕端等五代旧臣和宋朝宰辅相比,与真宗朝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抛弃原则依附皇权的馆阁词臣相比,杨亿作为西昆体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具有自觉的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体现出有宋一代士人典型的气质人品,就像王水照先生所说的,"在政治上崇尚气节,高扬人格力量" 。我的看法是,馆阁作为宋初诗坛的中心,其核心成员从太宗朝到真宗朝,完成了由五代旧臣向北宋新进学士的转化;这正是宋代诗歌逐渐摆脱贵族趣味的过程。 二 至于西昆体与白体的关系,历来论者较多看到它们相互对立的一面。即使近年来提出重评西昆体的学者,也较强调西昆体"是对这种鄙俚、浅近的唱和诗风(指白体)的有意的反动","杨亿等人是以变革诗风为己任的" 。其实,诗风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一种新诗风的产生,不仅意味着对旧诗风的颠覆和否定,而且也是对旧诗风某些因素加以继承、吸收的结果,是旧因素在新条件下的转化和改造。王水照先生说:"宋初诗歌三体,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固然是对唐人的心摹手追,仿佛步武,即使是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新变派'开始的'宋调'创造者们,在创新欲望的支配下,仍表现出对前代诗歌传统的崇奉" ,精辟地揭示了宋代诗风演变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其实,宋诗的生命在不断求新求变,不仅宋诗与唐诗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对西昆体与白体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可以这样说,西昆体正是在白体的基础上演化产生的,两者互相渗透,相斥相融,并行发展了一个时期,最终催化了宋诗的独立。 杨亿作诗,初从白体入。杨亿在真宗初咸平年间(998-1003)所作诗即为白体。与之酬唱的李宗谔、张咏、晁迥、李维、张秉、丁谓等入皆由学白体入,李宗谔就是宋初白体诗唱和领袖李昉之子。与杨亿相知的时相王旦即认为:"如刘筠、宋绶、晏殊辈相继属文,有贞元、元和风格者,自亿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这里所谓"贞元、元和风格",应是指中唐元稹、刘禹锡、白居易的诗文。尤须强调的是,在咸平之前数年的太宗淳化二年至三年(991-992),王禹偁贬官商州期间,所作的白体诗已以讽谕为主,主盟一时,影响极大,其后,咸平元年(998)杨亿知处州,至三年(1000)召还拜左司谏,外任仅短短的两年间,今所传诗作,如《民牛多疫死》、《狱多重囚》、《闻北师克捷喜而成咏》等,多为干预时政关心民瘼的作品,一改宫廷唱和诗风,其诗歌内容及风格取向,正与王禹偁商州诗"多涉规讽"相一致。这些诗作表明,像杨亿这样的馆阁文人,只要具备适当的生活基础,学白体完全可能由吟闲适之意向重讽谕的传统转化。 同时须知,在朝廷上下迭相唱和、杨亿亦浸淫白体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学习李商隐诗了。据其自述是在太宗后期:"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由是孜孜求访,凡得五、七言长短韵歌行杂言共五百八十二首。"(江少虞编《宋朝事实类苑》"玉溪生"条引《杨文公谈苑》) 这段自述说明,就在杨亿大量写作白体诗时,在仁宗至道年间(995-997)他已接触到李商隐诗,并甚爱之。真宗咸平四年(1001)杨亿初知制诰后,与余恕同主持考试,"因出义山诗共读,酷爱一绝云:'珠箱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击节称叹曰:'古人措辞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诗话总龟》后集卷五引《杨文公谈苑》)景德二年(1005)修《历代君臣事迹》,杨亿受命为实际主持人,适为他以"史笔"自任、以古喻今创造了最佳的条件,白居易诗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唱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不过与王禹偁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创作趋向已从现实转向历史,从地方转向馆阁,这就是时人所说的"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 (田况《儒林公议》),一部《西昆酬唱集》中的杨亿诗,正式显示了他由白体入,并与学习李商隐诗最终合一的实绩。西昆体实际上是白体、义山体(包括唐彦谦体,见后)混合的产物。 尽管白体诗风并未因西昆体的出现而被"截断",在宫廷诗苑,一直绵延到仁宗朝仍未消歇;然而在杨亿笔下,诗歌的题材已由外任时期仿白体讽谕诗的关心现实、体察民瘼,变为馆阁吟唱中多涉规讽的咏史述怀、借物言情;其形式也不再取白体的浅俗、闲雅,变为义山的感慨深沉、华美精致了。 当然,西昆之流行,不仅缘于杨、刘诸人的个人喜好,又与宋初科举尚蹈袭唐代旧制有关。太宗、真宗朝,朝廷省试仍为诗赋、帖经、对策三场,而实以首场诗赋定其取舍,于是律诗、辞赋、骈文风靡一时。杨、刘以学李商隐相标榜,适当其会,其"风采耸动天下",诚非偶然。欧阳修曾追忆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愈)文者。余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记旧本韩文后》)除科举原因外,就创作心态言,西昆诗人的身份较宋初白体代表人物更文人化,更合于宋代文化的内转趋势。这突出体现在重视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 "凡昆体,必于一物之上,入故事、人名、年代,及金玉、锦绣等以实之"( 《瀛奎律髓》卷十八),"非才高学博未易到此"(同上卷三)。以杨亿而言,"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博闻强记,尤长于典章制度,时多取正。"(《宋史·杨亿传》)杨亿自己也曾谈及在学养方面的有意追求:"精励为学,抗心希古,期漱先民之芳润,思觌作者之壶奥。"(《武夷新集序》)而既有内秀、又有外美的李商隐诗,适以学养为本,杨亿评玉溪生诗"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宋朝事实类苑》引《杨文公谈苑》),洵为知言。 故尽管真宗尚白体之平淡,不取西昆之典雅,下诏戒文章浮华,并在一些酬唱场合有意冷落杨亿,但西昆体仍能大行天下,后进者驰逐不已。于是,"国家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宋朝事实类苑》引《杨文公谈苑》);连欧阳修也盛赞西昆?quot;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六一诗话》),王安石晚年也不免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