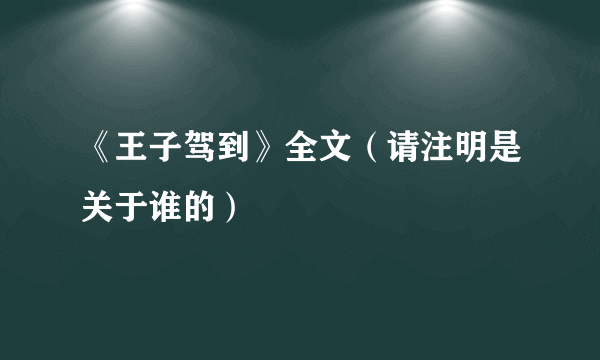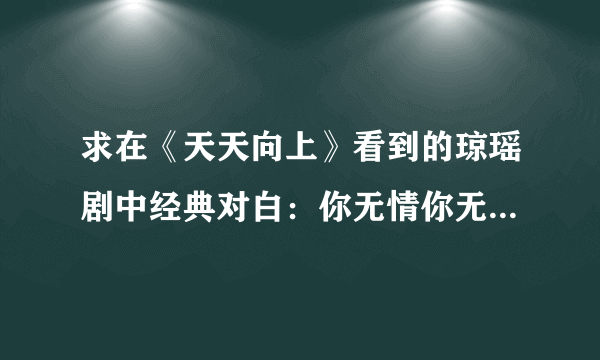消失宾妮远灯行全文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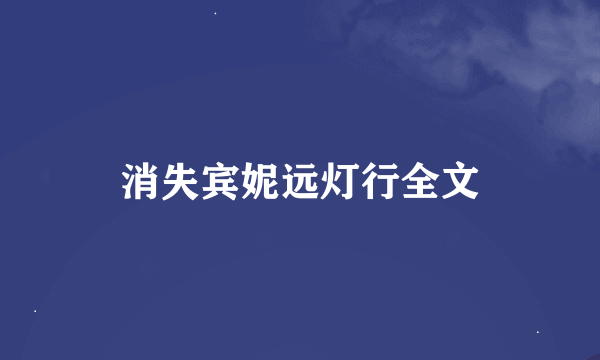
时迁走近我。她将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拉我依在她的肩头。她很瘦,嶙峋骨割伤了我的忧愁。我不出声。我知道她正将花朵别在我的发间。时迁试过几次之后,最后又将花取下,放回我的手心。 “它太顽皮了。总不肯听我安排。” 摊开手掌,柔嫩的花瓣像是被搓揉过的碎纸片。叶之芬芳携着少许酸涩,就这样驻留在我掌心的漩涡中。 那是我与她相识后不久。她那时穿着一身白衫,裙摆处断裂的布条已经扎在了我的伤口处。这一年我十岁。我因任性离家出走,我得以在困苦时遇见这个城镇上见不到的人。她在暗林之间长大,彷若一朵幽静的花。 我总是不知,为何这个镇上无人知道时迁的存在。她不知何处来,亦不知要去往何处。那一身白裙子亦是我偷偷从家里偷出来的交换。她救我时弄破了她的衣裳,于是我从母亲晾衣的架子上取下了它,送给了时迁。 我时常在母亲睡后,从窗口溜出去找时迁。她喜欢领我去青轨处。 在镇东有条暗青色的废弃铁轨。青苔不知何故攀爬上那条故人遗留的轨迹。时迁总是说起青轨的故事。在乡间有这样的流言,若要抵达幸福的彼岸,顺沿着那条暗青色的轨道一直走,轨道终于何处、何处便是彼岸。 时迁总是牵着我的手说:“我是要去彼岸的人。” 我不知什么是彼岸,只知伏在铁轨上嗅着它的气息,想嗅得关于这片大地更多的信息。然而时迁却将我拉起,用手指从铁轨上抹一丝在指尖,而后放在我的鼻前。 “地上太脏了。”时迁解释道,转而看向如此认真的我,“你在嗅什么?” “嗯。这里好像有死亡的气息。”我亦认真作答。 她稍作停顿,转而将那点腥绿抹在了我的鼻尖。 “撒谎呐。这里只有一个关于幸福的传说。” 呛人的生涩之味往心口涌去,我屏住呼吸努力擦掉她的恶作剧。再转过身去,却看见时迁又穿着那件破旧的白衫跑至了远处。她踏过的地方芬芳随风扬起,最终落在我身上。而我如同一个拾取她轨迹的顽童,以气味为向导,跟随者她往前跑着。 然而这直到多年后,我们才知晓。 其实我真的嗅得到。 童年快过去时,深桐才出现至我们的视野之中。他是村人在邻镇长大的独子,由镇之西面来。镇西是何处。与那青之轨迹截然相反的地方。时迁对他的经历起了兴趣,执意要去问他镇西的故事。 那是夜,我们像窃贼似的将少年堵截在路边。时迁盘问着少年来。然而面对时迁的伶俐姿态,少年竟在我们面前窃喜起来。他笑时皱了皱眉,眼神里收纳下时迁蛮横时的模样。 深桐的头发很短,露着光洁的额头。眼镜眯一眯就好像跳过了一个世界。我躲在时迁身后看着他,只感觉时迁的手忽然一紧,然后便是她冲上前去扭住了对方的衣领。 “不许笑!” 深桐不害怕。女孩纤细的小手握在他胸前,目光里是一片涂炭。他举起双手装作投降,小声说道:“这位女侠,对不起。” 他未成年的时候,声音柔得像某种小动物的哭泣声。 时迁这才放下手来。 深桐咳了一两声之后,眼角又浮过连绵的笑意。他抛下了一句“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姑娘呢”便消失于我们眼前。待时迁回过神来,眼前只有深桐逃之已远的身影。 后来时迁带我去逮深桐。 我在一端路口,时迁守着另一端。时迁知道我没能力抓他,只叫我发现他便大喊。于是我躲在路口,张望着小小少年的身影。然而直至月已当空,我仍然蜷缩在那一堆废弃物之中,依仗着微弱的星光辨别远方。 这一年,我仿佛是十一岁。 我渐渐有些害怕,中耳摸索着起身,才发现身体已经僵直得难以动弹。抬头往远方看去,天竟那么黑。远处的河岸边好像有无数星火飞舞,那约莫是萤火虫的光芒 再之后,我转身,十二岁的深桐出现在我身后。 他那日表情异常严肃。我慌张地往后退缩,张口却哑言。这才想起他应该是不知道时迁的计谋的。然而我未及将台词想好,他却先声夺人,扣下我之心弦来。 “喂。我说你,是叫什么来着?” 我鬼使神差,竟低声答了他。 “清远。” 年少的深桐笑了笑,他走上前来拉我的手,然后静静道:“你们输了。时迁没抓住我,已经气得回家去了。你也回去吧。” 那时他是十二岁的少年,穿一件深蓝色的袍子。风鼓鼓而来,肿胀在他的袖口,我一度以为他之手心将涌动出什么惊奇来。我仍然记得,那夜的一阵风朝我袭来。深桐踏过的地方,气息是圆润如花之蜜汁,他们被风高高扬起,而后重重地落至我的心上。这位好心的少年他将我送至河岸,嘱咐我好生回家,而后松开我的手,让我一人沿着木桥过去,穿梭与萤火之间。 再转身时,他仍旧在那里。 十二岁的深桐在流火之岸,朝我挥别。 辗转至第二日,我才知道我被深桐骗了。时迁在清晨时从房间的窗口爬进来,将我摇醒。我睁眼看着她的模样,白裙子仍旧破而脏,脸上还粘着河岸的泥土。 她将我自那一夜萤火中唤醒,气势汹汹地问:“你怎么自己走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个中缘由。定然是少年在路的另一端遇见了时迁,料得此处有我。于是辗转而来,稍稍点拨便将我处理掉,而后名正言顺地逃脱困境。反而是时迁,她笃定我将坚守彼岸,最终落得在蚊虫堆里等了一夜。 由此,时迁开始了与深桐的战争。 我不觉得这是战争。只觉得好玩儿。那个大我一岁的少年仿佛有种未知的力量,会将我预备作出的防御消之于顷刻间。他大约也是知道的。他总是故意地支开时迁,而后找到我。少年牵我去往河岸,而后为我指出回家的路。他仍喜欢在流火之岸嘱咐我早些回去。 而我竟那般乖巧,自黑暗里回到家中去,等着受伤的时迁又爬过我的窗户,让我为她清洗伤口。 “真的,我一定要叫那个深桐死了才好!” 时迁趟在我的床上,一面嗷嗷叫着、一面发着狠毒的誓言。而我将那些混着她之血液的水浇灌在墙角长出的那一截倔强之上。透明红的汁落在翠绿的叶脉间,滴答掉落。我模糊地知道她的誓言不会灵验。 因为深桐是不朽的少年。 自我的记忆之中,他是与萤火为伴、以长月为友的,不朽少年。 我原以为我们将永远这样愉快地斗着法。然而十三岁时,我们终于驶往命运的正轨上。那一年的某夜,母亲推门想来看看安睡的我,却发现了我与时迁的秘密。 时迁却像是一只蛾子,张着白翅抖落着鳞片飞离了我的房间。她的白裙子在夜光下荧荧舞蹈,母亲没看清她的脸,然而裙边某处镶嵌着母亲针法的边却露了出来。 第二夜。我试图开窗出逃,却发现这唯一的途径不知何时已被封上。隔着模糊的窗纸,我仍能辨得出远方的林木森森之处,萤火幽幽之光,却无论如何也出不了这间空房。半夜时,隔着窗我看见了那个熟悉的影朝我跑来。 “时迁,是你么。” 我站起身来,想隔着窗纸的虚影给她我的轮廓。 “我在这里。窗被封上了,我出不去。” 然而我站起身来时,却看见窗外暗红色的零星光辉点点而来。仿佛是乡人的火把,长如火龙,自时迁的身影后一字排开。 而后。我仍然站在窗里,轻声唤:“时迁,你身后的是什么?” 火龙随着时迁的消失而消失。我仿佛听见她逃窜时熟悉的步伐,然而她的双翼尚未打开,火龙便层层圈圈绕至她的身边。再之后,黑暗转瞬而至,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就这么自一层窗的距离间,与真相失之交臂。 再见时迁已是隔日清晨。我终于可以从大门跑出,待我慌张地抵达河岸,却看见那一身破旧的白衣自下游淌了过来。 “我没事。” 这是时迁见我时,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绕着她转,想看她身上是否还有零碎的伤口。然而她拉住焦急的我。 “我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那时她以湿漉漉的手牵着我,赤足踏过浅浅的河流,引我去另一岸。在我之寻找的彼岸处,深桐正站在那里。 “清远,是深桐帮了我。” 我抬起头,深桐的笑容仍然如蜜汁般芬芳诱人。然而我不知如何回应,因为待我明白过来时,他早已介入了时迁的心事间。 那夜村人将时迁捉走,因为我偷的那件衣裳。我不知道深桐怎样救了她,而后才得知,深桐是村长的侄子。我不大懂得一个孩童究竟能争取到大人的世界的几分信赖,只知道时迁真的没有受伤。虽然她仍然只能在夜间出没镇间。 十四岁那年变得格外漫长。 我的发辫长了,终可变成冗杂的髻。而时迁性懒,从不打理她的长发。半夜我们时常跑至河岸洗发,以清水濯净尘埃。时迁的长发如水草蔓开,分外妖娆。而后来她替我绑发辫,自头顶盘踞成不一的形状。 深桐觉得无趣。那日萤火虫漫天,他便顺手抓来,又取了水草编了个小笼子,将萤火虫放入笼中,而后悬在我的发间。我看着自己水中的倒影,额傍两处像是镶了两颗夜明珠。时迁夸我好看,深桐想了想,牵着时迁去了彼岸。他们留下我在此岸奔跑。因为时迁说,也许奔跑起来会更美妙。 他们立于彼岸,朝我喊道:“跑吧!” 我似流火。在此岸飞奔而去,也不知前方何处。为了他人的流火之梦,我跑了许久,跌了几次,发髻也散了下来。那两点星光也不知遗失在来路的哪一段。最后捂着我破败的残发跑回了家。一路不理会他们在身后的呼唤。眼泪在纷扰间大滴掉落下来。 我终于明白过来,那是嫉妒。 因而发辫散了我也不知,火光落地我也不知。我只知心口灼灼燃烧之味,燃烧着我脚底的卵石,仿佛要将我之爱意烘培成菜肴,给另一岸的人儿们美餐。 原来,我喜欢深桐。 次日我睡至饷午。母亲叫过我一次,我不肯醒。只裹着薄薄的被单在床角浅眠,寻找梦里那条河岸,寻找深桐送我回家时的身影。后来醒过来,是因为听得有人在敲我的窗。我睡在床沿,看着窗纸上人影渐渐显清,我确认不得究竟是时迁还是深桐。 他们那时一般高,一般瘦。 我等着人影离去,而他却久久侯在窗口。又过去一会,他从地上捡起树草之叶,贴在我的窗纸上,似是要传递什么信息。我渐渐坐起身来,看着窗纸上单薄的黑影渐成人形,小小的脸儿小小的手,长发盘在头顶。而后,他又在头上两处悬了两个圆形。 我知道,那是我。 我奔至窗边,推开窗,看见深桐蹲在我的窗下笑我。 “这样你才肯开窗啊。” 我敲他的头:“谁叫你们戏弄我。” 他躲闪开来,接而站起身来。这一下,他挡住了我的窗口。远方的明日在他身后,这崇山峻岭也在他身后。我脸庞仿佛因这不通畅的气流而平添了许些温度。然而深桐俯下身来看着小动物一般的我,看至我瞳孔里的流光暗转、心事徒生。 他拿出一只幼小的笼子,里头装着只萤火虫。与他昨夜做的那只精巧笼子不一样,这只笼子拙劣得很。 “别生气了。”他递给我,“你跑得那么快,时迁担心死了。” 我接过笼子,却发现上面镶嵌着一朵小花。白色。柔嫩的花瓣舒展开来。仿佛一道熟悉的誓言。 在这一瞬,我才明白,我们之间那样曲折。 我喜欢深桐。而我亦喜欢我的时迁。 而那个带着时迁的小礼物来见我的深桐,他是喜欢时迁的。 那夜之后,我心甘情愿地站在河边,让时迁替我盘上发,让深桐替我放上萤火。我像是孱弱的火苗,在他们面前缓慢燃烧。时迁不再让我奔跑,而是牵我的手在河岸边漫步。我跌撞一点她都扶着我,生怕我头顶的火光会消逝。 “清远像是盏夜明灯。”深桐道。 “清远是我的明灯。”时迁忽然意味深长地说着,“我仗着她为我寻路。” “她不认识路呢。夜夜都是我送你们回去的。” “可我并非要找到回家之路的人。”时迁将手握得紧了些,而后终于说出她多年的秘密:“深桐,倘若我要带着清远去寻找彼岸,你会知道去彼岸的路吗?” “彼岸?” “是的。深桐。我要牵着明灯一样的清远,到彼岸去。”时迁忽然笑了起来,“那里有我的母亲。” 彼岸是青轨的尽头。深桐在白日找我去认路,大约是惦记着时迁的话。我顺沿着铁轨往远方看,嗅着深桐柔润的气息。 他自花丛中细细的辨着每一处起伏,只为着让夜归之路不再崎岖么。 “你时常这样认路?”我追上去问。 深桐抬起头。只是笑。仿佛是笑我从未想过,他怎会那样顺畅的行走于黑暗之中,领着我回家。 “深桐……很喜欢时迁吧。” 他不答。而是指着路之远处满心欢喜地告诉我:“这一处曾经有过一个传说呢。” 他不理会我的优柔,也不回应我的疑惑,而是故意讲叙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来打消我追逐的眼神。他说多年之前曾有一位少女,因爱上有妇之夫而备受良心谴责。他们相爱却无法平息内心的愧疚私奔而去,最后善良的少女选择自己离开此地,让自己所爱之人永远幸福。 那一夜有人看见,一路上有星光庇佑在少女身边,仿佛神灵在替她开出一条出世之路。而少女就这样怀着深切的爱自我放逐。因她的离去,这段爱情虽不完满却饱受人尊敬。 “所以呢,他们说彼岸就在此路的尽头。” 深桐细细地描绘着。然而我听不下这样离奇的故事。我只知此情此景,我的手被握在他温和的手心之中,而他唇间细语像是一阵迷离的咒。尽管他是为他人之爱才牵我在此,然而我仍然轻易地忘记了一切。 寻找彼岸的那日终于到来。 我与母亲又有了无法歇治的争斗。自母亲与父亲分离,我们沉沉而活。于是我的生活仿若是沉静的湖泊之水,死于困顿,却因风起波澜。而母亲却成了这湖之深邃,亦是这风之狂野。那夜我欲从窗口逃走,却撞上母亲在窗外拦我。她料定了我会逃走,因为这已不是一次两次的任性,我终将远行。 可我仍然离开了。 踏着纷飞的草叶,我不顾一切的奔跑起来。往着每日与时迁约定好的地点。夜间沁凉的河水可以平息她日日焦灼的心,然而我的来到却点燃了她心里的渴望。 “我们走好吗?离开这里!”我恳切地拉扯着她的衣角。 于是这一夜,我们在黑暗的草丛之中游走。远处低沉的野兽呼唤之声,脚下是暗青色的铁轨。四周凛冽之势的山峰拼凑出一条狭长的道。原来我过去生活的城镇在这样狭小的一处山谷之中。 她笑着:“你害怕吗?” 我摇头。我在五年前便知我将出走,那时若非时迁,我已经客死异处。 但我仍然捏紧了她的手。 时迁看出了我的忧虑。 “清远,我是无家之人,你明白的。”夜风袭人,以时迁的气息浇灌着我懦弱的忧虑,“我要去彼岸,因为那里有我的母亲。即便今日不是你要我去,那或者明日,便是我要你随我远去。”我点点头。 这样半夜过去,我困倦的停下脚步来。时迁见我劳累,便让我小歇。我于是这样睡去。眼前一切随着闭眼的瞬间渐行渐远,内心却终究平息下来。 我满心欢喜,因为这一夜,我们已出落成十五岁的少女。十岁时我们在萤火纷飞之夜出走,如同暗夜的灵,自这人世间穿行而过,只留下苍茫的过去在回忆之中,妄图去寻找远方的彼岸。 但谁能料到,睁眼时,我却只看见深桐。 少年仍旧笑得蛊惑人心,我正贴在他的后背上,仿佛一只被捕猎的小动物。我朝四处看去,这世界却没了时迁的人影。 深桐笑我:“你是想喂野兽么。我听说这谷里的野兽都爱食猪肉的。” 我冒上火气,匍在他的后背咬他的肩头,但他不动。深桐仍然笑:“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我还以为时迁是随着你一起离家出走了。” “你替母亲来捉我?” “不。我只是打算来找你们。”他又笑,将我往身上抖了抖,我仿佛凌空的鸟雀,稍微纵身却又被捕捉,“原本想送你们出逃的。却只看见你睡在路边。这我就不好办了,倘若我帮了你,那不像是我们私奔似的?” 我心里一惊。私奔。 然而话语甜蜜的掠过心头后,一连串的疑问却接踵而来:“你来时没见着时迁?” “没有。” 少年甚至没有回头看我。那日打风吹起他忧愁甜蜜的气息,让我自他的后背上越发害怕起来。 我被送回家。母亲对我不闻不问。她不感谢深桐的壮举,亦不过问我的忧愁。她日日似从前,清晨时打水洗衣,傍晚时做饭烧水。偶尔看我一眼,望穿我对她沉静生活的厌倦。然而她不回答,亦不改善。 她是位妥协的妇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困守我,教我生命之含义。 我与深桐时常在河岸之边等时迁出现。深桐怀着甜蜜的笑替我盘发,替我挂上萤火之光,然后牵我在河岸之边行走。他说这样可以唤来时迁,因为“清远灯”是属于我们之间的秘密。 但她终究没有出现。 我们等待良久,最后丧失了信心。那几日城镇里有诡魅的传言,说传说中的狐狸精来到了镇上。又过几日,便传言那狐狸精要嫁入深桐叔父家中。 深桐见我闷闷不乐,带我去婚宴酒席。 我们为散心而去,却见美艳的新娘子着红衣而来。礼数过后,深桐牵我去偷看新娘的容貌。我们打赌她是否是芳华卓越之人,然而盖头掀起来之后,深桐那温厚甜蜜的气息却忽然转而黯然。 那新娘竟是失踪已久的时迁。 那夜又似浓墨般黑暗,我早早等在了河岸,因为我知晓深桐定然会在这里。为着这突然的变故而伤心。他比我所预料还要悲伤,他早已在河岸边编织了好多只小笼子,放好萤火虫。他制成了流苏一般的萤火之光,提在手中。另一些仍挂至我的的发梢。我默不作声地跟随着他。我知他是在召唤着那个希望依仗光芒而来的人。 然而长夜过去,那人却不曾来到。 “也不知发生了什么。” 深桐在河之尽头终于开口,他抚摸我的额发,替我理清一知半解的情绪,而后静静地看着我,“你别担心我。我很好。” 才不好。我嗅得到。 可我却出不了声。因为我妄图说些什么的时候,却见那个不朽的少年手中萤火掉落下地。笼子两两三三的破开来。而少年却忽然埋头在我肩膀,声音仍是笑的:“清远,我们还未来得及向她说些什么呢。” 我们身边流火如夜灵缓慢腾空,如画卷般绝美。而我亦不知,我有幸与深桐一起成为这故事中的人。虽然他念及的仍然是别人的姓名。 “我总以为时间还很长,我还能改变得了时迁呢。” 可他究竟要改变什么呢。 然而未及思考,一阵微暖的气息撞上我的耳垂。少年在我耳边低语。 “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之后是,十六岁,十七岁,再十八岁。 而后我听闻,每一个地域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性格,而我一直不知我们这个地方所拥有的是什么。只是在时迁离开我们之后,我与深桐仿佛渐成了没有主张的人。与母亲无异,与他人无异。与这城市里其他的人无异。 我曾经有过蒙昧的念头,总以为丢失了时迁,我们就渐渐沦为了普通人。深桐仿佛终究淡薄下感情。他仍然笑,仍然牵我手在城镇漫游。仍在流火之岸与我挥别。 只是我们不再在深夜游走河岸,不再见过时迁。我们偶尔听闻时迁的故事。她是不讨人喜的新娘,是没有子嗣的狐狸精。 直至几年之后,听闻乡间传说,说暗夜的河边有狐狸精出没。他们见着美艳的新娘点着幽幽绿光漫步河边,她手不执灯却有着火光相绕。好不可怕。 那夜。我与深桐相约河岸。 因为我们都明白那个传说的含义。那是时迁在召唤我们。 这是时隔三年之后的相遇。我们再见她时,她已是美艳的妇人。白衣脱去,而身着红衣。萤火之光在她的发间耳畔,映出她红润的面孔。 她叫我们:“清远。深桐。” 我未哭。深桐也没有激烈的心境。我们走至一起,我替她摘下头顶的光,然后打开笼子,放逐那星光点点。深桐亦不语,只是看着多年前曾经蛮横倔强的少女。他深知她如今也如那般倔强。某一瞬,我嗅见空气里辗转而来的两股熟悉的气息,他们又一次散发着浓烈的芬芳,然而此次,却忽然暗暗纠葛至一起。 然而她并不解释。时迁的话语那样清晰细微,亦是平常语气,仿佛不过是希望我们摘一朵花般轻易。 “我希望你们帮我,我要杀一个人。”着红衣的时迁道。 这是告劝不住的。无论时迁,或者过往。过去的尘封之事终于向我们展开。 原来出走的那夜,在我睡去之后,时迁听见了母亲的召唤。她一个人往路之尽头走去,却在某一处岔道上,看见了寒森森的尸骨。 “我知那是我的母亲。”时迁道,“她的灵魂告诉我一切,嘱咐我为她复仇。于是我嫁入了仇家身边。这样过去了三年。如今终于到了时间。” 夜晚的河水凉意袭人。 “那是我多年来寻觅的彼岸。原来彼岸存在,而母亲尚未抵达。于是才会留下我在这一方土壤上独自成长。”时迁轻描淡写道,“你可明白吗?我一直不知为什么只有我独自活在这世上,为何母亲去了彼岸留下了我。可,原因竟是这样。” 然而深桐仿佛并不意外。 “你这样下去,也没有尽头的。” “我知道你不会答应,多年前你就不答应。”时迁话锋凌厉,“我的仇家不正是你的亲人吗?你早已知道我的身份,才待我那样好吧。” 我抬起头来。 这个故事,其实深桐早已告诉过我。时迁亦告诉过我。 他们彼此告诉我一半,乡间流传着其余的部分,但是我却未曾将一切拼凑成章。深桐的故事之中,有位恋上有妇之夫的少女,最后为了彼此之间的恋情而选择了自我放逐。然而这位少女,竟是时迁故事里被逼死在路沿的母亲。 深桐从亲人处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堂皇处,而时迁自母亲的灵魂中得知了这故事的残忍,唯独我什么都不知。 只以为我们将永远这样,我恋着二人,他们却恋慕着对方。我心甘情愿的为他们两人付出。我以为一切不过是寻常的成长之路,我以为不过是普通的青春年华,然而他们早已早我一步知晓彼此之间深深的羁绊。 所以深桐才在那夜,伏在我的肩头叹息,再改变不了她。叹息的不是令她不走、不舍,而是他一直在我身边默默地想要使她忘却仇恨。然而却是我领着她,去往了寻找母亲的那条道路。 我低下头,“那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呢。” 我话语轻轻。时迁却分明听得动容。 她走过来拥住我,用着十四岁那年的语气温柔地说:“我要到彼岸去。清远,我不需你为我掌灯,只想你替我开路。我只想完成母亲的夙愿,替她求以公正,而后带她去彼岸。你们帮我离开此地。” 清远灯。远灯长行。 “待我到达彼岸,我会来接你。” 她走过来。将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拉我依在她的肩头。她仍旧那么瘦,嶙峋骨割伤了我的忧愁。她的红衣上芬芳气味早与幼年不同。但那语调气息却使我沉沦之中。 那之后的某个黑夜,乡间有一人死去。那人却是多年前神话的主角之一。 而我亦是在多年之后才知,那人竟是深桐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