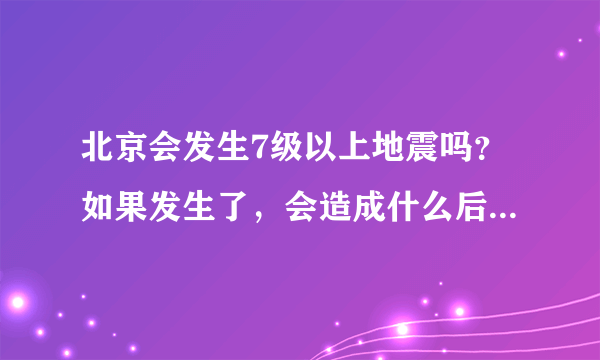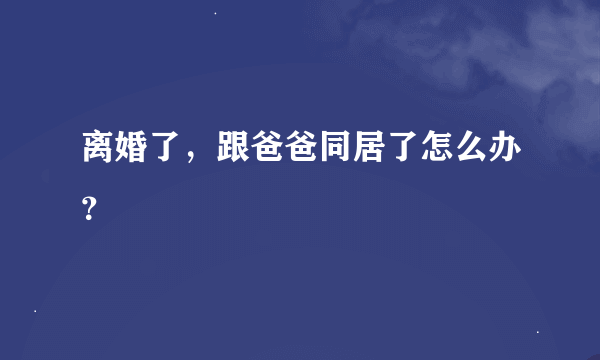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是什么意思?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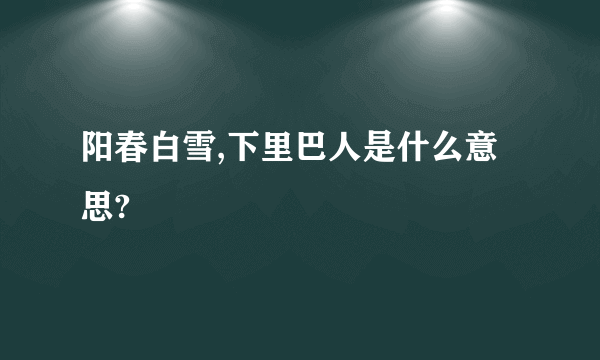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是古代楚国的歌曲名,屈原的大弟子宋玉曾著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一词后来被用来泛指通俗和高雅的文艺作品。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乱坦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 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丛友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当然宋玉与楚王的这番讨论的目的不是谈论歌曲本身,而是强调雅与俗的巨大差距,并为自己的才德不被世人承认而辩解。宋玉进而说"鸟有凤而鱼有鲲",自然非凡间俗物可比。宋玉说,"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最后,宋玉引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夫圣人 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宋玉的意思是,但凡世间伟大超凡者,往往特立独行,其思想和行为往往不为普通人所理解。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中指出,《宋玉答楚王问》中明明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即有客人在郢中唱歌。而不是郢人在唱歌,更不是郢人善唱歌。沈括认为,郢中为楚国旧都,"人物猥盛",之所以和者寥寥,是由于不知道或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宋玉 以此自况,未免有些不讲道理。以郢人不熟悉阳春白雪这样的曲子而指责他们,这不是很荒谬么?沈括还指出,阳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细节后来被错误的解读和传播,例如,善歌者都被称为"郢人",而原文的意思是郢人不善歌。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一书中所指出的:"观听殊 好,爱憎难同。" 对于听惯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当然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毛 泽 东 试图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统 一 起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 一 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 一 的问题。不统 一 ,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统 一 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在#极#左#的年代里阳春白雪成了受批判的对象渗陪槐,而下里巴人也成了政治的附庸。 阳春白雪虽然被指高雅艺术,但古曲《阳春白雪》在很多书籍里被解题时,都称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很显然这是在"阳春白雪"四个字的字面上解题了。阳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阳春 白雪》年代相隔太远,已无音乐上的关联。 《阳春白雪》曲倒是很有可能与元代的散曲有关。元代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是一本著名元代散曲集。元曲在曲韵及格律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阳春白雪》中收录的白仁甫的《驻马听》中有这样的句子,"白雪阳春,一曲西风几断肠。"可见元代已有阳春白雪这支曲子。 至于元代令人"几断肠"的《阳春白雪》曲,如何演变为今日轻快流畅的乐曲,已非大路所能参透。言犹未尽,此处且做"留白",与众友共赏析。 《阳春白雪》是由民间器乐曲牌仪《八板》(或《六板》)的多个变体组成的琵琶套曲。 阳春白雪:由民间器乐曲牌仪《八板》(或《六板》)的多个变体组成的琵琶套曲。“八板头”变体的循环再现,各个《八板》变体组合在一起形成变奏的关系,后又插入了《百鸟朝凤》的新材料,因此它是一首具有循环因素的变奏体结构。 《阳春白雪》流传有两种不同版板,“大阳春”和“小阳春”,《大阳春》指李芳园、沈浩初整理的十段、十二段乐谱。《小阳春》是汪昱庭所传,又名《快板阳春》,流传很广。这里介绍的是《小阳春》。 ===============================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是古代楚国的歌曲名,屈原的大弟子宋玉曾著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一词后来被用来泛指通俗和高雅的文艺作品。这里的“巴人”一般被认为是生活在长江和峡江地区的巴国人,巴人当时是如何地唱歌,早已经无处可以考证,就连巴人的来龙去脉,因为至今没有可以参考的古籍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谜团。 三峡工程的蓄水倒计时推动了峡江地区的考古进程,近几年来巴人之谜也逐渐地浮出水面,专家们认为在商代,中原王朝并没有对峡江地区拥有控制权。到了春秋战国,峡江东段的居民受楚国文化影响,也就是刚才宋玉提到的下里巴人,下里为楚国的民间歌曲,巴人也就是峡江地区的巴人音乐了。巴人虽以渔猎为生,但峡江地区的盐业为巴人提供了经济保证。据说,巴人不纺织却有衣服穿,不耕作却有粮食吃,当时的盐业就像是今天的石油业,巴人“鸾鸟自歌,凤鸟自舞”,一派歌舞升平。但是也是因为巴人的盐业使得周围的几个大国垂涎欲滴。自对巴人地区的考古工作展开以来,巴人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也有专家认为巴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峡江的西面受蜀文化的影响,许多专家认为巴蜀文化是不可以分开来看的。战国后期秦国和楚国为夺取巴人的盐业使巴人两面受敌,巴国内部也发生内乱,秦楚皆借此机会占据了大片巴人的土地。历史上曾经有巴将军蔓子以许三城来借楚军平定内战的故事,但事后巴蔓子以剑自刎,用自己的头颅来答谢楚王,以保住三座已经许给楚国的城池。 巴国的最后消失是在秦统一中国的前后。但是峡江地区的盐业一直持续到廿世纪晚期,“盐巴”已经成为一个中文中固定的词汇了。 今年的六月下旬,四川宣汉县的罗家坝又有关于巴人的惊人发现。笔者有幸立刻奔赴现场,先睹为快。罗家坝是长江流域渠江支流的一个坝子。1999年曾经有过一次考古发掘,2001年,国务院公布“罗家坝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四川考古所又接到发掘300平方米的任务,其目的是为今后的罗家坝的整体规划做前期工作。今年的发掘自三月份起,由队长陈祖军主持,宣汉县博物馆配合。陈队长一行由摄影、绘图和修复师组成。考古队租用农家房子作为基地。今年的发掘因为期间受到盗墓的影响,可以视为两期。前期也就是按计划的300平方米的发掘,一共清理了32座墓葬。据陈队长的初步估计,今年所涉及的范围中可以看到历时五百年的变迁。其中有几座墓葬主人遗骨上留有明显的战死痕迹。 四月下旬在三百平米发掘区以东九十米的地方发生了盗掘,立刻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注意,经过四十天的跨省侦察,最后将疑犯捕获于河南郑州。因为四月下旬的非典型肺炎所设置的公路、铁路、水运的检查,盗贼没有将所掘赃物运出当地。最后根据疑犯所交待的线索,公安人员在罗家坝的河坝中找到了七件被盗掘的青铜器。据说,盗贼当时挖到这批东西后,因为其精美程度和非凡的价值,当即被吓得全身哆嗦,知道一旦被捕有可能小命不保。 在公安人员开始立案侦破的同时,陈队长也对被盗地点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也就是今年的罗家坝二期发掘。笔者抵达罗家坝时,正值发掘进行到最高潮阶段,虽然天降暴雨,笔者却兴奋异常。自公路下得车来,眼望着河对面的考古工地,因为隔着一条渠江的支流,河水正在暴涨,当时的感觉是如同投奔水泊梁山一样,好在现在有电话可以不用朱贵的隔岸一支箭,在河边的老乡家打了个电话给陈队长,一会儿果真见到罗家坝方向划来一支小船。船家问我是否害怕河水之汹涌,他岂知笔者有十年的长江水手生涯。陈队长打着伞在河坝上等着我,抵达基地时已经是全身湿透。 陈队长向我介绍了情况。他认为被盗贼所搅乱的遗迹应该是一个祭祀坑,暂时被定名为K1,坑的中心有三具人的尸骨,坑的南部放置着大量的青铜兵器和少量的陶器。坑的填土中含有大量的木炭,估计和祭祀仪式有关,在掩埋过程中,曾向坑内抛掷过一些动物肢体和陶器。 次日,渠江支流的河水继续暴涨,陈队长下令:强行提取坑中物品。笔者目击了考古人员的紧张工作。成绩是出土了一百三十来件铜器,一批饰件、彩绘陶器和生活用具。因为该坑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的,加上规模,实属前所未有过的发现。 自今年三月至七月陈队长一行进驻罗家坝近四个月,野外之辛苦有目共睹。陈队长本人是1985年的北京大学考古历史系的毕业生,自从事考古事业以来,已经主持过数项重大考古发掘。其实,笔者一直是非常敬重严谨治学的考古学家的,自少年时代起,曾经幻想过学习考古,幻想有朝一日奔赴考古现场,去与古人谈话,检讨得失,议论人生。可惜,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笔者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考古这一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借摄影报导之机会, 与陈队长一行同吃同住, 同享发现之惊喜, 也圆了我少年时之梦想。 一周之后, 笔者离开了罗家坝, 陈队长亲自划船送我至河对面乘车,考古队还有些收尾工作要做。笔者继续行程,奔向重庆的涪陵和湖北的茅坪,那里也有笔者要跟踪的关于巴人的痕迹。中华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巴人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一支,巴人也是你我祖先的一支,无论是下里巴人也好,还是阳春白雪也好,这些如同涓滴细水汇成长江,不尽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