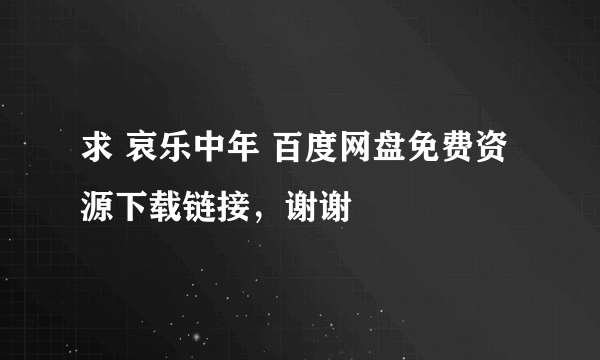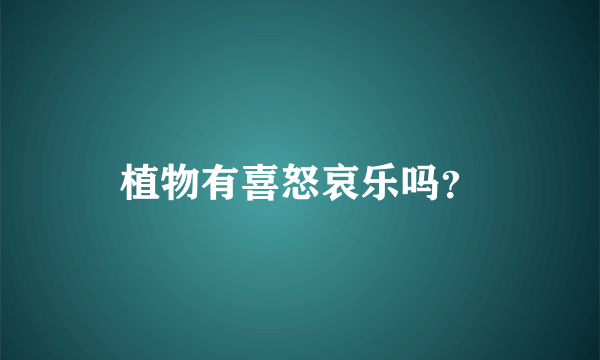嵇康声无哀乐论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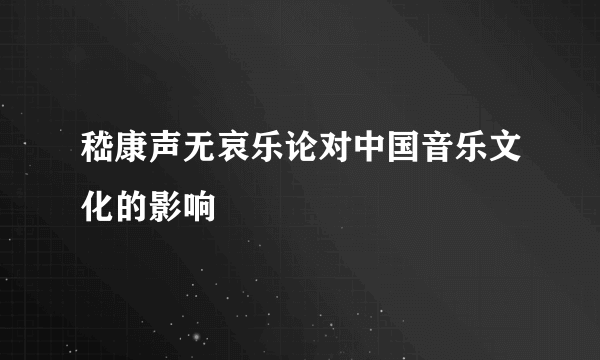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魏晋玄学名篇。“声无哀乐”不仅是竹林玄学而且是整个魏晋玄学的主要论题。一直到东晋,人们仍在讨论这个论题。《世说新语•文学》:“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嵇康之论“声无哀乐”是有的放矢,其论之“的”为作者假拟之辩论对予“秦客”。秦客诘难所之,多为儒家礼教思想。其要旨上在夸大音乐教化作用(“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基础之上,贬低音乐鉴赏者的能动作用(所谓“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人之情感靠音声激发,受制于音声。嵇康针锋相对,提出“心与之声,明为二物”,“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 《生无哀乐论》由八组辩论组成,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的八次问难和辩答,了论述音乐的表情功能和社会作用,音乐欣赏的主观和客观性,人类听觉和视觉、嗅觉、味觉之间的关系,感情表达和音乐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等等方面的问题。他针对儒家片面夸大音乐的社会作用,提出音乐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人的感情是主观存在,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即“心之与声,明为二物。”“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由此提出了“声无哀乐”的论述观点。文中的“秦客”实际代表了传统的礼乐观念,即声有哀乐。而“东野主人”则是嵇康自己的化身。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观点,会更加具有一种真实感和说服感。也更容易和全面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嵇康的思想,有着典型的道家思想。嵇康厌恶现实的社会,崇尚无为和出世。所以,他才会隐居山林。嵇康在这篇论著中,也提出了“无声之乐”的观点。和声无象。这点,与老子的“大音希声”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他反对儒家的一些思想。文章的开始,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 而其中一句『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盯尘音哀以思。』出自《礼记•乐记》,原文如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不顺,不和谐);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秦客以此来问难作者,古人皆认为声有哀乐,你为何会有不同的想法呢?这不是违背礼道吗?《礼记》是儒家一部经典作品。对于这段话,”他认为,“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 声音是无相的,但是人的心有哀乐之分。用悲哀的的心情去听音乐,那么音乐也就是悲哀的了。对于孔子闻韶,他说,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後叹美邪?就是捉,虞舜的美德人人皆知,而不用非得听了音乐才能知道。由此可知,嵇康的这部作品,就是从否定儒家开始的。这也这个是玄学道家的主流意识。魏晋玄学时期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时期。嵇康作《声无哀乐论》可以说是从音乐鉴赏的角度,大胆肯定主体意思的存在,将“心”从“声”的制约与统奴中解放出来,从而在音乐鉴赏中获得主导地位。嵇康认为,听音乐的人心中原本就怀有或哀或乐的情感,所谓“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哀心有主”;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这一观点是说,人心中先有了哀乐,音声本身并无情感,它只起诱导和媒介的作用,使它表现出来。对于作曲者来讲,是心中先有了“哀乐”,然后将自己的这种情感融入到创作当中,通过音乐的创作手法,如:旋律、节奏、和声、音色等的运用向人们传递着其对自然界、对内心情感以及对外部世界等的感受。而对于听者来讲则是由于听到音乐之后而产生了“哀乐”之情。例如:当《粱祝》的音乐响起时,听着长笛吹出的鸟鸣般的华彩音调,不由地从脑海浮现出一幅风和日丽、桃红柳绿、百花盛开、鸟语花香的迷人画面;而听着大锣、大提琴和大管奏出阴暗的音调以及铜管严厉、粗暴的音色时,心中会不由而生一种不安的情绪。因此,人实际感受到的,只是自己内心的悲哀而已。强调‘心’与 ‘声’二者的区别,认为‘声’是客观的东西,‘心’是主观的东西。二者不可混同。在认识论的领域,必须严格区分“主”与“客”,“能”与“所”。嵇康有见于此,从肢纳两方面作了阐述:一方面,凯饥禅他指出,不能把主观的情感加于客观事物,把它们说成是客观的属性。他说:“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于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则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则谓之怒味哉?” 就是说,不能以主观爱憎来判定人们的贤愚,不能因醉者的喜怒而说酒有喜怒之味。同样,也不能把主观的哀乐作为声音的属性。另一方面,嵇康认为,客观的物质运动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他说:“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所谓“上生下生”,是指六律六吕按“三分损益律”而有“黄钟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簇”等关系,以十二律同十二月相配,中吕位于四月,但决不因为人们在冬天吹中吕之律,它就变音了。嵇康强调了乐律的客观性,指出音乐有其内在的和谐秩序,是不以人的哀乐之情为转移的。作为儒家音乐理论的代表,《礼记•乐记》主张声有哀乐,其《乐纪篇》讲圣人“致乐以治心”,音乐之或哀或乐“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听音乐的人只需被动地接受“拯治”就足已,无须发挥什么能动性,更不需要什么主体意识。这样一来,音乐的效应就只剩下“治心”,嵇康主张声无哀乐,意在强调鉴赏主体的主导作用,救儒家乐论之弊从而体现魏晋“人的觉醒”的时代精神。嵇康在强调鉴赏主体之“心”的能动作用的同时,也并不忽略音乐之“声”的心理效应。嵇康讲“声无哀乐”并非说音乐与人的情感无关从而否认音乐对人的心理效应。他认为音乐对人的这种心理效应不是哀乐,而是躁动与安静、专一与散漫等。音声“简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从这点可以看出嵇康仍然肯定了人在听觉感受中对音声情绪上反应,而这种“躁情”的情绪反应,是不同与哀乐的情感体验的。嵇康谈“心”与“声”之关系,其出发点与儒家正统乐论不同,后者着眼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嵇康则从音乐的感觉要素(亦即形式结构)和听觉形象入手。《声无哀乐论》对音乐形式结构的总体描绘是:“(五音)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音乐作品能为人心所感知的诸种感觉要素,如节奏、旋律、和声、音色,以及它们所组合而成的特定的音乐形象或听觉效果,都包含在“单复高埤善恶”这六个字当中。《声无哀乐论》以琵琶筝笛、琴瑟之体、齐楚之曲、姣弄之音为例,具体讨论音乐的感觉要素及其心理效应。 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卸数节,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钟鼓骇心,故故闻鼓之音,则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闲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役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 不同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或者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乐曲,引起欣赏者不同的心理效应。正统儒家的音乐理论家在夸大音乐教化作用的同时,也忽视了音乐的艺术形式,而在看待欣赏者情感与音乐形式之关系这一问题上,音乐教化理论同样失之简单、肤浅,所谓“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教化,则以垂涕为贵”。嵇康主张“声无哀乐”,否认了“心”与“声”的表面联系(所谓“音使我悲,声使我哀”),而以玄学家和音乐理论家的慧眼,看到了“心”与“声”的对应。综上所述,嵇康对于“心”与“声”的关系问题,是分两个层次认识的,即音声自身运动对人心理情绪上的影响,为第一层;而音声与人的情感之间的关系,则是对心声关系的第二层认识。嵇康的音乐思想在《声无哀乐论》中作了专门的论述。在这篇论著中,他首先提出“声无哀乐”。的基本观点,即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哀乐是人们被触动以后产生的感情,两者并无因果关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然后,又进而阐明音乐的本体是“和”。这个“和”是“大小、单复、高埤(低)、善恶(美与不美)”的总合,也即音乐的形式、表现手段和美的统一。它对欣赏者的作用,仅限于“躁静”、“专散”;即它只能使人感觉兴奋或恬静,精神集中或分散。音乐本身的变化和美与不美,与人在感情上的哀乐是毫无关系的,即所谓“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那么,人的情感上的哀乐从何而来呢?嵇康认为这是人心受到外界客观事物的影响,具体说是受政治影响的结果,即“哀乐自以事(客观事物)会,先遘(相遇)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人心中先有了哀乐,音乐(“和”)起着诱导和媒介的作用,使它表现出来,同时,他还认为“人情不同,各师其解,则发其所怀”,人心中先已存在的感情各不相同,对于音乐的理解和感受也会因人而异,被触发起来的情绪也会不同,所以他认为音乐虽然能使人爱听,但并不能起移风易俗的教育作用。即“乐之为体,以心为主”,“至八音会谐,人之所说,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本不在此也”。在上述问题上,嵇康大胆地反对了两汉以来把音乐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甚至要它起占卜的作用,完全无视音乐的艺术性,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而且他所看到的音乐的形式美,音乐的实际内容与欣赏者的理解之间的矛盾等,都是前人所未论及的。只是他对某一方面做了片面的、夸大的理解,从方法论来讲则是诡辨的。嵇康的思想存在着矛盾:他曾反复提到“先王立乐之意”,并把音乐分为抽象的“至乐”—“无声之乐”与具体的音乐—“音声”两种。人们在当前听到的只是“音声”。另有一种“至乐”是古代理想社会存在的音乐,其本性是“至和”或“太和”,它虽与人主观的感情没有因果关系,但因那个社会的政治是理想的(贤明的),即“和”的,所以人的感情也是“和”的,是“和必足于内,和气见于外”的。通过“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的途径把“心”与“至乐”统一起来,所以这种“至乐”虽然也只是起诱导人心中已有的哀乐情感的作用,但与政治能很好地统一起来,没有什么矛盾。例如古代的“咸池”,“六茎”、“大章”、“韶”、“夏”等,都是“先王之至乐”。能够“动天地感鬼神”。而“音声”则是现实社会存在的音乐。现实社会的政治不是“和”的,所以人们的感情也是不“和”的,音乐与政治存在着矛盾。嵇康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是从音乐方面去解决,而在于改良政治,政治清明,就能产生“和”的音乐。嵇康站在反对派的立场,攻击了那种不管自己政治的好环,拼命反对民间音乐的儒家正统思想。反对他们以音乐的哀乐为借口随便给音乐加上“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罪名。他指出,“郑声”是美妙的,而对美的喜爱又是人的天性,所以它能使人迷恋,但与“淫邪”无关。有的音乐之所以“淫邪”,那是“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的结果,也就是统治阶级不良统治的后果。把责任推到了当权者的身上,在当时确是很大胆的。但是对于民间音乐,他也认为必须对它加以控制、窜改,所谓“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损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就是说,可以让它存在,但要以和谐为标准,不必曲尽一切变化,对于过分美妙的声音要加以修改,使人感觉快乐而不放纵,所以嵇康对音乐的看法仍育其阶级标准的。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不仅仅讨论了音乐有无哀乐、音乐能否移风易俗,还涉及音乐美学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即音乐的本体与本质问题,音乐鉴赏中的声、情关系问题,音乐的功能问题等,提出了“声无哀乐”的观点,即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哀乐是人们的精神被触动后产生的感情,两者并无因果关系。用嵇康的话说,就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 音乐本身的变化和美与不美,与人在情感上的哀乐是毫无关系的。嵇康认为人的情感上的哀乐是因为人心中先有哀乐,音乐起着诱导和媒介的作用,使它表现出来的。嵇康大胆反对了两汉以来把音乐简单等同于政治,完全无视音乐的艺术性,甚至要它起占卜作用等方面,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并且他所看到的音乐形式美、音乐实际内容与欣赏者理解之间的矛盾也是前人所未论及的。《声无哀乐论》反映出的主张音乐脱离封建政治功利的音乐思想与主张“礼乐刑政”并举的官方音乐思想,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音乐美学思想两大潮流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