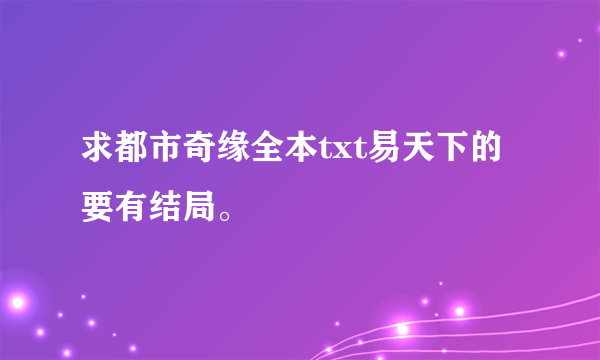一路疼,一路爱的结局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第二天,白可睡到中午才起床。陈敏和沈重九已经坐在桌旁等她吃午饭了。三个人的眼睛都微肿。 陈敏看两个孩子沉默得异常,挤出笑脸说:“这几道菜都是妈妈精心准备的,你们快吃啊。”她说完,沈重九没有动,白可拿起筷子,夹了菜,却没有送进嘴里。 做好了某种决定的样子,她放下碗对陈敏说:“阿姨,我想把我的车卖了。” “卖车?那你怎么去德州。飞机场和火车站这些地方都是有警察的。”陈敏说。白可突然的放弃没有让她高兴,她反而开始为她考虑起来。 “你的病更重要,”白可说,“等你病情稳定了我再走,报纸和电视上不是报道过有人徒步穿越美国吗,我也可以。” “不可以。”沈重九开口道,“那样要走到什么时候。” “不管多久我都会坚持下去。”白可回忆起米奇家乡的传说,坚定地微笑着。 沈重九和陈敏对看一眼,陈敏很快移开目光,放下筷子说了句抱歉,匆匆离开客厅。她实在无法再演下去,无法看着白可真诚的笑脸而无动于衷。她也是有一个女儿的人。 大口大口吃着饭,白可要为之后与病魔的战斗积聚能量。 “白可。”沈重九忽然正色道,“你要留到什么时候?” “直到确定阿姨没有生命危险了。”白可说。 “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现在?” “对,现在。”沈重九没有看她,“早上医院打电话来说,她的病是误诊。只是有一点胃出血罢了。” “真的?” “真的。” 粘在嘴角的米随着她的微笑,掉落在碗中。 换好衣服,整理好行李,白可站在门前与她的弟弟以及弟弟的母亲道别。 “你要照顾好阿姨。”她嘱咐。 “他还小呢。”陈敏笑道。 “不小了。记住那句话,树欲静……” “知道了知道了。” 沈重九打断白可的话。他指了指白可的衣领说:“你怎么把那玩意儿缝上了。” “这很好看啊。”白可低头看看领口边刻着英文的扣子。 “可是……”沈重九盯着那颗扣子,把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改口说,“你走吧,路上小心。如果累了就回来,我和妈妈一直在这里等着你。我们一起庆祝独立日。” “好。”白可抱了抱沈重九,又抱了抱陈敏。坐在车里依依不舍地看了他们半晌后,发动汽车重新上路。 蓝色的轿车在视线里逐渐远去,陈敏问:“你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 “你不觉得真相对她太残忍吗。”沈重九说。 “我突然发现,”陈敏回过头,“你好像成熟了不少。” 沈重九微微一笑。人不能总是沉迷在自我的世界中,当我们老陆学会关注周围的人事物,并被其所震撼时,成长便开始。他庆幸加入了这场游戏,但同时也对白可感到深深的抱歉。 望着远处那个淡蓝色的点,他轻声说:“去冒险吧,姐姐。” 他相信她能够胜利。 五月的骄阳下,一边是高大的铁架电网,一边是神秘的空旷厂房,她行走其间,把自己想象成异次元时空的战士。经过工业区后,星罗棋布的野花从草地里冒出头,观赏着明媚的春光,而它们自身,也成了路人眼中的风景。 白可情不自禁唱起了家欢快的小调:“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 遥远的前方,蓝绿的背景下突显出一团红色的影子。白可向仿早挡风镜外探了探头,确定那确实站了一个人。这荒凉的废弃公路上,人迹罕至,要在这里搭到顺风车怕是很难。她放慢车速靠近男人的方向,直到看清他举着的牌子上写着:堪萨斯。 “你是要去堪萨斯吗?”她停下车问男人,得到确认后,她招了招手,“上车吧。” 男人欢呼一声跳进车里。他个子很高,一坐下就让前座的空间显得狭小。 “嘿,我叫热拉尔?伯纳德,你叫什么?”男人热情地打招呼。 “我叫白可。”白可笑着看他一眼。男人长着满脸的胡子,只有从眼睛才分辨出他是不是在笑。他的额头和颧骨的线条刚硬分明,很有东备含雀欧人的味道。滑稽的是,这样一个粗犷的男人却穿着卡通T恤,胸前有一个大大的蝙蝠侠的标志。 “你是中国人?”热拉尔问。 “对,你呢?” “我生长在美国,但有一半法国血统。” “难怪你的名字这么独特。” “谢谢。” 男人伸展胳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非常怯意的样子。 有个人作伴,旅途中的疲惫减轻不少。热拉尔是个很健谈的人,时常妙语连珠,逗得白可哈哈大笑。 在笑声中,车开过俄克拉荷马城,再行进几个小时,就要靠近德州边境了。她既兴奋又紧张,手心不停出汗,转动方向盘时微微打滑。 “累了?”热拉尔察觉出她的紧张。 白可羞赧一笑,不知如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 “我来帮你开吧。”热拉尔说,“你一个女人孤身上路肯定很辛苦,我帮你开一会儿,反正也快到德州了。” “那就谢谢你了。”白可没有推辞,她怕自己这么激动下去,指不定会把车撞到哪根柱子上。 男人开车往往有一些特定的习惯,比如听歌,比如照镜子,热拉尔的习惯是来根雪茄,但是找来找去发现自己忘带了,嘴里闲得慌。 “你有口香糖吗?”他问白可。 “没有。”白可说着,翻了翻挡风镜的前零碎物品,找出一罐维生素片,倒出几粒说,“维生素片,要吗?” 热拉尔看了看她手里的红蓝药片,用目光研究了一会儿,他控制好方向盘的位置,头转过来,张大嘴巴。“啊……” 白可愣了愣。 他直勾勾地盯着她的手心催道:“快点。” “哦。”白可掌心一翻,把药片悉数倒入他毛茸茸的嘴里。 “好酸。”热拉尔的肩膀抖了一下,咂着嘴瞥了眼挡风镜前的一本诗集说,“你爱好诗歌?” “是。”白可暗暗搓了搓手心。 “我也会背几首法国诗,你要听吗?” “请讲。” “咳咳,”热拉尔咳嗽两声,提了一口气,声音洪亮地说道,“un petit mont feutré de mousse délicate, tracé sur le milieu d'un fillet escarlatte.” 短短的一句话,朗诵到此结束。 白可还在期待他的下文,他忽然语气一转得意地问:“怎么样?” “啊?呃,很好。”白可礼貌性地笑笑问,“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覆盖着纤细苔藓的绒毛般的小丘,中央有一条鲜红的小小的缝。”热拉尔用英文朗诵了一遍,不等白可反应过来,他捶着方向盘哈哈大笑。 他一笑,白可感觉整辆车都在震动,她往旁边躲了躲,心想这还真是个很戏剧化的人。 就在此时,“TX”的标志从眼前一晃而过,白可猛地转过身,只看到路牌一个隐约的轮廓。 “德克萨斯!”热拉尔高声欢呼着,仿佛他是刚刚征服了这片土地的国王。 抓住胸前的十字架亲吻了一下,白可激动得呼吸急促。 “太好了。”她克制住拥抱热拉尔的冲动,用开怀的笑容对他表达自己的喜悦。 “你一定是要去见很重要的人吧。”热拉尔说。 “是的,我丈夫在这里。我要去找他。” “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不知道,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他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慢慢来,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我相信你会的。” 说话间,热拉尔缓缓踩下油门。 白可好不容易平复下情绪,看向窗外时发现热闹的城区已经变为冷清的郊外,她问:“伯纳德先生,你家在哪里?” “就快到了。”热拉尔说。 66号公路经过德州的狭地,开车用不了几个小时就能穿过。当白可看到新墨西哥州的标示时,她慌了,对热拉尔说:“前面就快到新墨西哥州了,你是不是走错了?” “没有,没错。”热拉尔给了她一个安慰的眼神,“我家在新墨西哥州。” “可是我要去的是德州。” “我要去新墨西哥。” 热拉尔不容反对地看着她。 终于,白可意识到她载错人了。坐在她车上的绝对不是像他所说的是什么热衷徒步旅行的大学教师。 “那请你先送我回德州,好不好。”她软言好语地恳求。 热拉尔做出正在思想斗争的表情,好一会儿,他遗憾地看着她,叹了一口气说:“不。” “我把车给你,你现在让我下去。”白可更退一步。 “我不要。”热拉尔学着白可的声调,尖起嗓子。 “你到底想怎么样!”白可忍不住叫起来。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去德州。” “那我就想不让你去德州。” “你……”白可气得咽住,呼吸还没顺过来便吼道,“我帮了你,我从来没伤害过你,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你怎能这样!” “你知道这世界上,哪种人最可恨吗?”热拉尔偏过头,从眼角斜着看她,“不是明目张胆去害人的,也不是在背后捅刀子的,恰恰是那些伤害了别人却还不自知的家伙。” “我没伤害过你!” “哼。” 冷笑一声,热拉尔放缓车速,在路边寻找合适的旅店。 “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不管你想怎么样,都先让我找到我丈夫,好不好。”白可求着求着,发火地嚷起来,“我求你了,行吗!” “知道我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吗?”热拉尔问。 白可不想回答。 他笑着说:“你确定不想知道?” “叫什么。”白可翻了个白眼。 “俊面煞星热拉尔。哈哈哈哈……” 听着他张狂的笑声,白可整个人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选中一家高档的旅馆,他抓着她的手腕把她从车上拖下来。路边有警察经过,旅馆的大厅里也来回走动着警卫,白可正要呼救,热拉尔捂住她的嘴,在她耳边说:“你想清楚了,你之前杀了人,要是落到警察手里,这辈子都别想去德州。” 最后一句话说中了她的要害,眼睁睁看着一个警察从面前走过,她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 他带着她走到柜台边,要了间双人房。接待员看白可脸色不好,礼貌地问热拉尔:“需要帮助吗?” “没关系,”热拉尔说,“你知道,女人每个月总那么几天。” “狗屎。”白可低咒。 热拉尔一愣,尴尬地对接待员笑了笑。 拿了钥匙走进房间,门一打开,热拉尔把白可扔了进去,从外把门反锁。 白可试着撞门开,但徒劳无功。她坐在地上,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她不知道为什么倒霉的事总会发生在她身上,好像暗地里总有人在和她作对。 全身酸痛,她感觉很疲惫,看浴室的门开着,便走进去,洗了个冷水澡。 洗完澡,头脑清爽了些,她走出浴室便见热拉尔和衣睡在床上,四肢大开。睡着的男人像个孩子,偶尔咂咂嘴。 她想他对她应该没有淫念,或许他脑子有问题吧,是个疯子。 吃了点茶几上的三明治,她干坐在床边毫无睡意。为了让自己的神经放松,她拼命想着和唐一路在一起的时候,想着她被他抱在怀里,可回忆越是清晰,越是停不下来。已经很久了,她连他的幻觉都见不到。 想着他,在他若有若无的歌声中,她睁眼到天亮。作者有话要说:后天要去外地,所以今天把这两天的量都更了 1 [已购买] 屏幕上,身材娇小的女孩子在狭窄的客厅里安静地走动。像是才洗完澡,身上只套着一件宽大的白衬衫,刚能遮到膝盖上方,露出大半光泽的腿。 那是被他强迫出来的习惯。 他崇尚对身体的自由展露,他们同居以后,他为她买的衣服都是半透或者紧身的,短短的穿在身上,让她身材各个美好的地方尽情暴露在他眼中。对于他的私心,她自然是不知道的,和他谈判无果后,她自己想了个办法,就是穿他的衣服。 深爱的女人,穿着自己的衣服,在那个叫家的地方悠悠然地做着生活中各种细小而琐碎的活计,慢慢地,就这么一生一世了。只为这一世,他宁愿不要轮回。 放映机发出轻微的嚓擦声,屏幕上的女孩子经过沙发和茶几之间的空隙时,纤细的腰灵活一转,带动微湿的头发散落在颈旁。 她用手把长发捋到一边,露出那张让他魂萦梦牵的脸。 暂停键按在那一刻。 他半跪在屏幕前,手指一遍一遍抚着她的脸。他再一次爱上了这个女人。 开始他不敢相信这卷带子里记录的是她的生活,因为那个女人身上早就没有了他记忆中的唯唯诺诺,面对生活里的各种挑战,她理智而坚定。虽然有时候还会露出傻傻的样子,而那正式她蜕变中的样子。 “你是要长出翅膀了吗?” 指尖从她的肩头滑至她的背脊。凑到屏幕前,他把脸慢慢地贴在她的脸上。他能够理解唐一霆了,理解他为何会爱上单薄纸片上的虚幻的人。同时,他也明白,有很多事他都做错了。 曾经他以为相爱的两个人必须是紧密相连,不管灵魂还是肉体。最好可以把灵魂揉在一起,嵌进同一个身体,这样才安全,在这样安全的保障下他才能放心去爱。 可是他错了。这世上的任何事都要经过考验才能成功,他走了捷径——单纯地锁住对方的灵魂,逃避生活的风浪,就算成功也只会是过眼云烟。在不能相见的情况下,灵魂被分隔两地,他们却还能义无反顾地爱着,对彼此都充满信心,这样得来的爱才足够坚韧,才不会让他有即使握在手中还是会随风飘走的无尽担忧。 “唐先生……” 秦清推开门,随后愣住。她敲了很多次都没人应声,不放心地推门进来,却见唐一路抱着电视,着魔般的紧紧贴着屏幕。而墙上,连天花板,贴满了他妻子的照片。她真怀疑自己走进了一位神病患者的病房。 “唐先生。”她又叫了一声。 他显然是听到了,但并没有动,好一会儿才把脸从屏幕上移开,说:“你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 唐一路起身,后退着坐到床边,眼睛没有离开屏幕半刻。秦清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拿出一本书安静地读着。 稍后,有人敲门。秦清深吸一口气,放下书走到门边。 唐一霆站在门外看了看失魂状态的唐一路,他低下头,听到秦清在他耳边轻声说:“他从刚才就一直这样。” “没事的。”唐一霆说,“他是太久没见到那个女人了。不过很快,他就会忘记她的。” 不忘也得忘。 “麻烦你了。”唐一霆对秦清笑笑。 “不麻烦,不过……” “不过什么?有什么事尽管说。” “我想……”秦清的目光闪烁不定,“我想单独和你说一件事。” “单独?” “是。” 她从后把门轻轻关上,鼓起勇气,看着唐一霆说:“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你说。” 唐一霆没想到秦清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简单的考虑过后,他说:“没有特殊的事,他们一般不会上二楼来,有什么话你就在这里说吧。” 秦清一再提醒自己镇定,她望了望走廊尽头,那里有一处拐角,角落的墙壁实则是一面作为装饰的落地窗,窗前刚好可以站两个人。而楼梯在走廊的另一头。 “我们去那里好吗?”秦清指着拐角说。 唐一霆看了看,同意了。他们一同走过去。 透过落地窗,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柔柔的阳光落在波流暗涌的河中,反射出些微跳跃着的光华,如她此刻的心。 “什么话这么难说出口?”唐一霆问。他们已经待了快有五分钟。 “我想告诉你……”她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想起唐一路之前对她说的:“你只要看着他的眼睛,什么都不想,眼睛、鼻子、耳朵,通通都不要了,就只留下一张嘴和一颗心,自然而然地,你就能说出那些最难表达的话。”说到这里,他眨了眨眼睛。“特别是情话。” “你到底想说什么。”唐一霆耐着性子问。 “我可以叫你一霆吗?”秦清问。 虽然觉得有些无理,唐一霆还是点头了。 “一霆,”秦清深深地看着他如星的双眸说,“我喜欢你。从你出现在入学典礼那一刻,我就喜欢你了。” 微微的怔愣,唐一霆想起四年前德克萨斯大学入学典礼上的情形。作为三代华人移民的代表,他为一群青涩的中国留学生讲解美国种种先进的科技。当时他并没有对任何一个学生留下印象。真正注意到秦清,是去年,他从内州回来以后,第一眼便觉得,这女孩和那人有几分神似。 如果说着这句话的是那个人,他该高兴得不知所措吧。但是现在,他只能对她说:“我很抱歉。” 目光瞬间暗淡,秦清勉强微笑着:“我猜到会是这个答案。”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 “说了才没有遗憾哪。” “你们女人的想法真奇怪。” “那一霆……”秦清改口道,“唐先生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向来是不管看上什么,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得到手,绝对不会给她拒绝我的机会。” “可是这样也太霸道了。” “我有个朋友对我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我发现真正决定命运的,是手段。” 窗外的矢车菊依旧开得灿烂。秦清撇开内心失落的情绪,不断地找话题和唐一霆闲聊。直到一个守卫匆匆跑上来被唐一霆斥责:“没有我的吩咐这里不能上来你不知道吗?” “唐……唐先生,唐先生逃走了!”守卫语气急促。 “你喝醉了?脑子不清醒了吧。”唐一霆冷哼。 “是真的!”守卫拿出一枚银色的十字架。 缓缓地站直身体,唐一霆看着守卫手里的东西,想到什么,猛然看了秦清一眼,随即推开守卫向唐一路的房间走去。 只有放映机传出的些微声响,房间里空无一人。 他疾奔到楼下,找遍客厅和院子最后来到停车房,几个被打伤的守卫斜靠在墙上,车少了一辆,而剩下的都被利器戳穿了轮胎。 “他怎么可能走到这里?你们是饭桶吗,拦不住他吗?”唐一霆一把揪住守卫的衣领。 “对不起,唐先生,你们实在太像了,我、我们没认出来。” “饭桶!”他把他扔到地上,转头对墙边的几个守卫说:“我花那么大的价钱请来的就是你们这样的饭桶?三个人连一个病人都拦不住!一群只会吃饭的猪!” 被这样辱骂着,其中一个脾气稍硬的守卫冷笑了一声说:“你真确定他只是一个病人?” 没功夫把时间浪费在几个没用的守卫身上,唐一霆边吩咐人去找辆车来,边往前厅走。 一到前厅就遇上了黎祥,不等他说话,黎祥抢先道:“我没截住他。” “那你看到他往什么方向去了?”唐一霆问。 “我追他到飞机场,看到他上了去新墨西哥州的飞机。” “新墨西哥?他怎么知道白可在那里。”对这个问题没有过多追究,唐一霆立刻给热拉尔在新墨西哥州的家里打电话。电话响了十几声都没有人听。他吼道:“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伯纳德先生已经好几天没和我们联系了。”黎祥说,“我猜他临时改变了路线。” 唐一霆愤怒地把话筒摔在地上。“去给我雇一架私人飞机!”他叫着走出去。 黎祥默默看着他走远,手伸进西服的暗兜里,摸了摸里面的枪。他用这把枪指着唐一路时,唐一路已经逃到机场附近的公路上。 “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我的枪法可是你身为军官的爷爷教的。”黎祥掏出枪说。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唐一路面不改色:“黎叔,你想杀我?” “你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黎祥拉开保险。 “如果非杀我不可,能不能先等一等,等我见到她……” “如果你死了,所有的诅咒都不存在,一霆会把负罪感转换成对我的仇恨,这对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而且,你们再也不必为了女人而争执。”黎祥说着,一步步向唐一路靠近。 “听上去确实不错。”唐一路不躲不避,“那么算我求你,让我再见她一面,了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愿望。”1 [已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