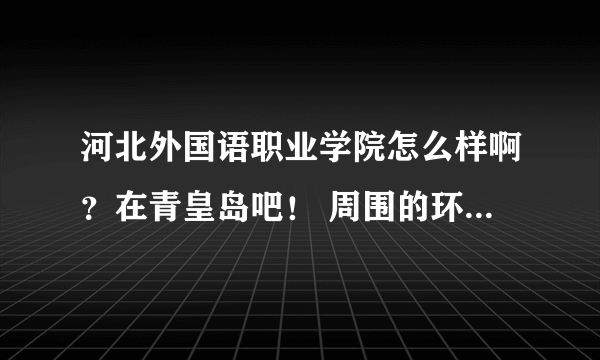比较《左传》和《国语》叙述风格的差异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一、导论王充的《论衡》案书篇有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由此句话可看出《左传》多记事,《国语》为辅助《左传》则多记言,两本书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此外,《国语》的观点或是文辞等方面更与《左传》大异,而两书对祥毁漏於相同事件的不同叙述角度更是有差,今举晋惠公改葬太子申生一事来做叙事比较,其大致上可分成事情的差异、预言的差异,以及功用的差异三点。二、事情的差异《左传·僖公上第五》记载:「晋侯改葬公大子。」,而《国语·晋语三》亦云:「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达於外。」共世子即是太子申生,因其諡号为「共」所以又称共世子,惠公则为夷吾,和申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观此两段记载可知惠公改葬共世子一事两本皆有纪录。然而,《国语》中有国人之诵及郭偃二事,而《左传》没有,又《左传》里有狐突遇太子申生一事,而《国语》没有,这便是它们最大的差异,即事情的差异。《国语》对改葬之事记了国人和郭偃的言论,其记载:国人诵之曰:「贞之无报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贞为不听,信为不诚。国斯无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贞,大命其倾。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岁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此段话是说国君虽想依「正礼」改葬申生,但申生的棺木却不断传出奇臭,国人便因此讽刺其国君窃取君位的「非礼」行为却还侥幸活著,余做再加上国家动乱不安,这种昏君不是国人所要的,而它们想要的是在狄国的那位重耳公子,并说出十四年后惠公将会失去君位之事。又郭偃曰:「甚哉,善之难也!君改葬公君以为荣也,而恶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实戴之。恶亦如之。谨烂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数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诸侯以见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数,言之纪也。魄,意之术也。光,明之曜也。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明曜以昭之。不至何时?欲先导者行乎,将至矣!」晋国的大夫郭偃更阐明说如果人有「善」於内心,必能传播於外,显扬於民众的道理来讽刺夷吾的不得人心,更以数、魄、光三项来预言十四年后重耳会回国继承君位,数是预言的纪录,魄是民意的先导,光是明德的闪耀,三点综合起来便说明了重耳才是人心所向的明君,而郭偃同时也呼吁民众,其想为重耳做先导的人须快点行动,因为重耳就快来了。在《国语》中,国人以及郭偃的言论除旨在讽刺夷吾之外,也拿他跟重耳做对照,说明人心和人民之间的关联性和重要性,一个君王如果内心善良,行为谨慎,人民就会爱戴他,反之,则会唾弃他。然《国语》对此一事件的叙事,到了《左传》却是从未出现,反而是不同的事,《左传》记载:晋侯改葬公大子。秋,狐突适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於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即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於韩。」对於改葬一事,《左传》反转而纪录了狐突在到下国的时候遇到太子申生,其告诉狐突说夷吾改葬他的「无礼」行为,故请於帝以罚夷吾,并要将晋给予秦,让秦来祭祀他,狐突便回答申生,且说明神不会保佑不是同类的人,而人民也不会祭祀不是同一族的人,况且人民又有何罪过,其滥施刑罚又缺乏祭祀,希望申生能再考虑此事,申生於是答应狐突会将再一次请求上天,最后上天允许申生惩罚有罪的夷吾,并说出秦与晋将在韩打仗,且晋国将会失败的预言。虽说《国语》和《左传》对惠公改葬太子有不同的说法,然内容却都扣紧「无礼」两字。晋献公在位时,申生遭骊姬陷害自缢而死,然其葬礼没有按照礼下葬,故晋惠公夷吾想依正礼改葬之,但惠公在这之前却背叛当初向里克、丕郑和秦国许下的诺言。起初,秦国派公子絷去慰问夷吾时,夷吾私下告诉公子絷曰:「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丕郑与我矣,吾命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君苟辅我,蔑天命矣!亡人苟入扫宗庙,定社稷,亡人何国之与有?君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到城五。」其上皆为《国语》里记载夷吾要重赂里克、丕郑和秦国以让自已成为晋君之事,又《左传》记载「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并告诉夷吾说:「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因此夷吾便答应要给秦国土地,而秦国接受贿赂自然也就帮忙「纳惠公」的事,里克和丕郑亦是,然而,惠公夷吾立了之后,却杀里克与丕郑,又背约不给秦国土地,并迁申生之墓,甚至在秦国闹饥荒时都不肯输米给秦国,乃得知夷吾背信忘义的无耻,并将当初许下的诺言一一弃如蔽屣,而过去他更曾与晋献公的夫人贾君通奸过,此种种为了政治利益的「无礼」的行为更与他想依「正礼」改葬申生作为形成强烈的对比。故两书的书写内容不同,但对於夷吾的不该却做出强烈的批判是其对事情看法一致的共通点。三、预言的差异在惠公改葬共世子的事中,《左传》与《国语》都说出关於未来会发生的事,《左传》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於韩。」,《国语》载「岁之二七,其靡有徵兮。」、「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数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前者预言了「秦晋韩之战」,后者则是「秦伯纳重耳」,同是预言但两者相差甚大。第一为预言的事情和时间不同,秦晋韩之战和秦伯纳重耳很明显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此外,秦晋韩之战是发生在僖公十四年,而秦伯纳重耳则是发生在僖公二十四年的事,两件事相差了十年,时间相距甚远。第二则为预言的表达方式的不同,《左传》是以申生请於帝来呈现,一个是已逝世的人,一个是上天的意志,换句话说,其预言是假藉神灵的方式来公诸於世,但《国语》则不然,其预言是藉国人及郭偃之口说出,两方都以「岁之二七」、「数」来道出十四年后的事,岁之二七便是指十四年,数是指成数,便是岁之二七,此外,郭偃曾云:「其数告於民矣。」又曰:「数,言之纪也。」可见国人是从「数」得知此预言,而「数」又是「言之纪」,即是预言的纪录,有此可见国人与郭偃是知道有纪录才能做出预言,与《左传》是有预言才做记录在书中的方式正好相反。再者,第三是预言基础的问题,从上可知两书会做出预言的原因皆在於晋惠公的「无礼」,《左传》说「夷吾无礼」,《国语》亦说其「贞为不听,信为不诚。」,贞,正也,意指夷吾想依正礼却不得认可,要立诚信却不见真诚,然而,《国语》又比《左传》多了「诚」和「恶」两项因素,「诚」是上述国人未见惠公真诚的缺点,后郭偃曰:「君改葬共君以为荣也,而恶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实戴之。恶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可知郭偃除了批评惠公无礼的行为外,亦说出惠公内心的「不善」来讽刺他的不慎行为,藉「善」来赞美重耳并与夷吾作对比,更突显出夷吾的「恶」,故知两书的预言在基础上还是略有差异,毕竟发言人不同也是其关键,申生是从替天行道出发,而郭偃及国人则是从人民的利益。虽说两则预言有差异,但还是有其相同之处,除上述皆以「无礼」做基础之外,两个预言分别在几年后也确实成真,虽时间点及发生的事情截然不同,但这两点可算是两书预言的异中有同之处。四、功用的差异经过上面两项的比较之后,便隐约可以看出两书想要对世人传递的意思有些许不同,也就是他们功用的差异。《左传》比较注重事的记述,言论的纪录倒是很少,其形式是类似历史事件的记载,也就是史事的记载,并就史实来发挥扬善抑恶的精神,事中的申生和狐突便是以正派的角色出现来惩罚夷吾,而《左传》对於恶的人也是会加以批判,毫不手软。相对地,《国语》则重在言的铺张,在惠公改葬共世子篇中,郭偃及国人的言论就占了大半的篇幅,然而,《国语》的功用和《左传》皆有抑恶扬善的精神,对好人便加以称赞,如郭偃云:「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明曜以昭之。」这句话是从正面来描写重耳,反之,对夷吾说出他已「恶滋章」了,可见对於坏人亦是会批判的,但《国语》除重言之外,《国语》在言论中会偏重阐明某项道理,因此功用上和《左传》又有差异,篇中的国人除说明凡事得依「正礼」的道理外,郭偃又提出一个人如果内心有「善」,人民就会爱戴他,这便是说明了人民是会依附「善心」之人的真理,国家要容易统治,国君自身修养是不可或缺的,由此又可看出在《国语》中「礼」与「德」是密切联系著的,其写出了夷吾的失德无礼,必失国的关系,所以夷吾最后才会失去王位。《左传》与《国语》在功用上的虽有些许差异,但并不会影响两本书的价值,它们的作用皆是透过对历史的真实纪录来呈现给世人,其内容以及阐发的道理等,对於后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五、结论透过不同角度的比较以及不同观点的叙述,《左传》和《国语》都各施所长的展现其不同的风格,不论是记事或记言,抑或是著重点的的不同,还是本身对事情的看法不同,它们留给世人的是多角度的历史观点,以及许多供人省思的道理,而究事情、预言以及功用上的差异得到了两书对於相同事件不同的叙事结果外,我们也可以从这历史的事件中得到了警惕,并了解到夷吾的种种缺点,他的无礼、他的背叛、他的忘义及无德,这些人心的丑恶面无疑是给我们警告,而重耳的善、礼、德则是给我们做人的良好模范,这些是可以运用在当今社会的。而即使事件的过程不同,史家对其解读不同,史书对其记载不同,结果却一定是相同的,一个人的善或恶关系著他的未来,而其作为也会被记在书上,而当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看这些事情时,相对地,我们也就多一个不同的思考路线,而更能呈现出一个多面的「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