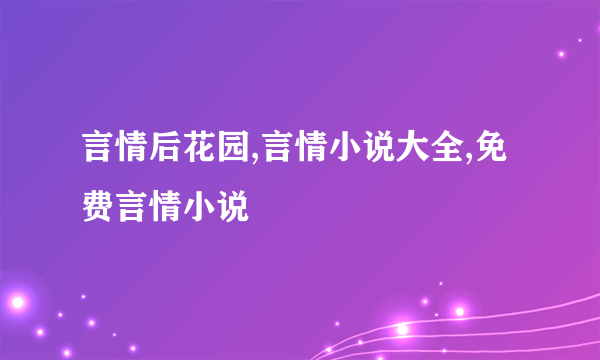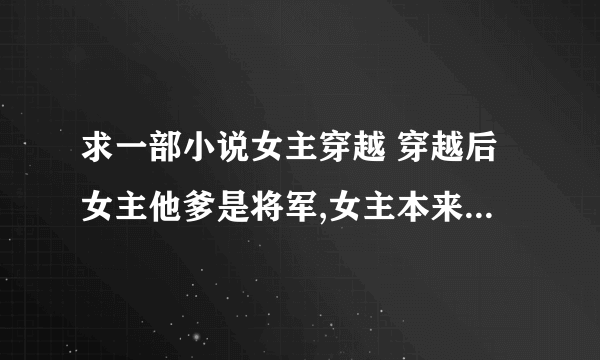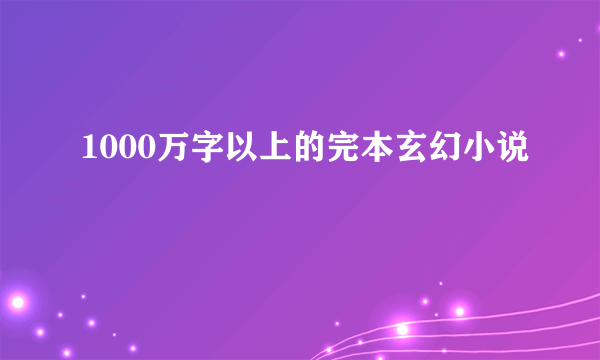求好看的恋爱小说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那是80年代初 我和她见了一面后,双方印象都很不错,后来我还约这个女孩看了一场电影。电影开始不久,我大胆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只稍稍反抗了一下,然后就任由我握着她的手直到电影结束。 很快,我们就频繁地交往了起来。每天天刚亮,我骑着自行车早早地来到她家楼下,等她下答颤楼后,我就骑着车子载着她把她送到学校。然后,我再骑着车子往单位赶。下午估计她下班了,我提前从单位赶到她的幼儿园,再把她送回家。 每逢周日,我还会约她出来玩儿,在公园里一待就是半天。我们两人坐在长椅上,紧紧地挨在一起,卿卿我我地聊着单位里的事,聊各自的家庭,也聊对未来的憧憬,总之有说不完的话。偶尔,见周围没人,我还会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摸一摸她的长发,或是搂一搂她的腰。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就在我们陷入热恋之际,我们之间出了点岔子。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邀请她去了我家,她见我家住房很拥挤,回家就把见到的情况向父母描述了一番。她的母亲觉得我家的住房条件那么差,就开始反对我们的婚事了。她是个没主见的女孩,在母亲的影响下,有一天她也吞吞吐吐地向我提出了这个最让我头疼的问题:你们家房子那么小,我们结婚后住哪儿呀? 在那个年代,一提起住房问题,与几乎所有的上海人一样,我的心中也就隐隐作痛。这是最让我们无奈和尴尬的事,特别在谈恋爱时,这几乎成了我们男人致命的软肋。像我家这样的特困户,更是难以启齿。 我们家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一家三代,老老少少五口人——奶奶、父母,以及我和还在上学的妹妹。另外,我还有个哥,不过他有路子,和单位领导的关系比较好,婚后不久就搬到单位分的一间小房子里去了,虽然只有七八个平方,但却让许多人羡慕得要死。 这么小的房子住着这么多的人,对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简直不可思议,大家的压抑感也可想而知。我与父母之间就隔了一块布帘,他们之间的偶尔的性生活尽管小心翼翼,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让我们觉察到了。 现在我的女朋友既然把这个让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了,为了在自己还没开始痛苦之前就结束痛苦,我来了个快刀斩乱麻,赶紧先宣布“吹”了她。那时到底是年轻啊,敢想敢干,说分手就分手。我也没跟她解释分手原因,只说我们在一起不合适,至于哪儿不合适,我死活也不愿意跟她说。 就这样,这个幼儿园老师跟我分了手。这次感情经历带给我的刺激就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有的山盟海誓都是假的,在房子这样的大问题面前都经不起考验。后来,再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索性直截了当把自己的住房条件跟对方说清楚了。这一招还真灵,果然我刚一开口就把对方吓跑了。这样折腾了一年,后来又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是纺织厂的,叫张素芳。介绍人把我的情况如实告诉她后,她竟然没有嫌弃我,愿意和我见一面。我跟着介绍人到她们厂一看,这女孩亭亭玉立,白净的脸上透着红晕,我马上就动了心。 初次见面,女孩对我的印象也还不错,于是我们就相处了起来。张素芳就像她的外表,是个温柔、纯静的女孩。她家离我家只有三站地,每天晚上没事时,我常会骑着自行车载她去外滩玩。那儿有一处著名的“情人墙”,我们的恋爱,就是从“情人墙”开始的。 所谓的“情人墙”,实际上就是一堵防洪墙,但这儿却洞举颤是那个年代上海最浪漫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成百上千对青年男女,就会悄然出现在外滩,开始上演如今的人们无法想像的“集体恋爱”的话剧。 “情人墙”的纳败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上海人生存空间狭小、普遍住房条件窘迫,两代人或三代人同住一屋习以为常,男女青年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如果到对方家里去,就必须在那些家人的目光关注下呢喃低语、眉目传情,其尴尬可以想像。没办法,既然住房紧张,那就到户外去。 那时的公园,除了盛夏,晚上一般都不开门。夜间公园开放期间,黑灯瞎火的地方也经常有民兵、纠察、联防队员来巡逻,以保证公共场所不受污染。那时又没有咖啡馆、酒吧、舞厅可泡,故而情侣们大量涉足的活动场所只有马路,于是“荡马路”就成了谈情说爱的代名词。 情侣们荡马路自然愿意荡到人迹稀少、灯光昏暗的所在地,这样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社会治安情况较差。到冷僻角落容易遭到抢劫或流氓阿飞的侮辱,或者纠察们过分热心的保护,不管情侣们是奋力反抗还是拔脚逃走,结果总是留下一段心有余悸的记忆,因此上海的情侣们不约而同地要找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地方,众志成城,外滩“情人墙”就慢慢地自然形成了。 “情人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恋爱场所,在这儿没有人打扰你,也不用担心会碰见熟人,因为大家来这儿的目的都很明确,那就是谈情说爱来了,因此也不怕别人笑话你。即使陷入热恋中的情男痴女们忍不住做出一些“出轨”的举动,如抚摸、亲吻,别人也会熟视无睹,因此在这儿谈恋爱,不仅安全,而且还会很轻松,不必有任何顾虑。 我第一次和张素芳接吻,也是在“情人墙”那儿。因为这是我的初吻,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清楚地记得,那天她穿着一身白色 连衣裙,在微风的吹拂下裙角轻轻地摆动着,我和她靠在一处昏暗的地方,我的眼前除了她飘动的长发,就是默默流动着的江水了。记不起那天我们究竟都聊些什么了,只记得在我们身边大约半米的地方,正有一对恋人抱在一起长时间地亲吻着。 大概是受了他们的感染,我也鼓起勇气,突然抱住了素芳,疯狂地亲吻起来。她像是被我吓傻了似的,忘记了反抗,等反应过来后,她不仅没有反抗,反而比我更加热烈地吻着我。这是我第一次亲吻一个女孩,也是我此生感觉最激情的一次接吻。 从那以后,每次去“情人墙”,我们都会激情地接吻,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有一次在“情人墙”那儿,我甚至还在亲吻她时,把手伸到了她的衣服里,摸到了她的乳房。不过,这次她没有让我得逞,而是狠狠地拿出了我的手,生气地骂我流氓,并警告我说,如果我以后再这样,她就不理我了。 我知道她是真生气了,从那以后一直到结婚,我再没敢做过类似大胆的举动。她对我这么厉害,我不仅没生气,反而还很得意,觉得自己的女朋友真是纯洁。毕竟,在那个年代,这个举动是绝大多数女孩都不能接受的。 经过一年多的交往,我和张素芳深深地相爱了。虽然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但我们的爱仍是那样的真挚,那样的情意绵绵。当然,除了“情人墙”,马路上、公园里、影院中偶尔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留下我们的海誓山盟。我们共同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共同向往着新生活的甜蜜。在亲人和朋友的一片祝福声中,我们携手走到了一起。 我结婚的时候,住房情况比后来在北京地区热播的那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反映的还要糟。张大民住的是大院,好赖还可以通过挨一板砖挤出一块地方盖那么一间小屋。而我们家住的是楼房,只有那么一间房,总不能像张大民那样,把楼下的空地给占了吧? 那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楼房里,没结婚时,我们一家五口的床是这样摆的:我妈和我爸睡一张双人床,我奶和我妹睡一张双人床,而我则独占一张单人床。三张床摆在一起,中间用布帘隔起来,睡觉的时候把帘子放下来,白天则把帘子拉开。平时做饭都是在走廊过道里。 三张床紧挨着摆在一起,能留出的空间已经不大,仅够一个人侧着身子走过去,现在如果要结婚,必须得把我那张单人床换成双人床,那整间屋子肯定一点儿地儿也没有了,大家只能从床头下床,而床头则又要摆着桌子、椅子这些家什,晚上起夜,黑灯瞎火的,一不留神就会撞到上面。 事实上,我的这个担心并非多余,结婚那阵子,张素芳就因为不熟悉“地形”,好几次晚上起来到外面方便(小便可以尿到尿盆里,大便就得下楼到公共厕所里去解决了)都撞到了床头的桌子上面,把上面的碟子碗的撞得稀里哗啦地响。 这些生活上的不便,说起来还都是小事,克服一下也就习惯了,关键是这么拥挤的居住环境,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夫妻的性生活。妻子是个十分“讲究”的女人,她一直习惯不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和我做爱。晚上,她从不让我碰她。 她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充分得让我无法反驳:我们的旁边就睡着奶奶和妹妹,而隔着奶奶、妹妹,就睡着我的父母,我们的每一个动作,发出的哪怕最轻微的响动,除了耳聋的奶奶,所有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和她在晚上大家睡觉时过性生活,那不明摆着告诉大家我们正在干什么吗? 我身高一米八,在单位又爱打篮球,身体很壮,是个性欲很强的男人。晚上睡觉时,看着身边躺着的娇美的妻子,很难耐得住诱惑,常会忍不住对她动手动脚。这时,她总是打着哑语,指着布帘那边的家人,示意我不要这样。有时,我不听她的劝告,想霸王硬上弓一次,她就会生气地拧我的胳膊。我虽然被她拧得很疼,但也只能忍着不敢叫出声来,我怕家里人听见,影响他们的休息。 当然,妻子也不是个完全“不讲理”的女人,有时她看我猴急的样子,也会很同情地帮我解决一些问题。她允许我在大家都睡着了的情况下,轻轻地抚摸她的乳房,或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用手帮我把那些积蓄已久的东西释放出来。除了这些小动作,偶尔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妻子被厂里评为三八红旗手,得到了一张奖状,那天晚上她很高兴,竟然允许我真正地做了一次。那天深夜,等大家都睡着了,我慢慢地帮妻子脱下衣服,然后又悄悄地趴到了她的身上。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小心极了,没发出任何声响。 妻子那天感觉也特别好,我刚趴到她的身子上,用手摸她的下面,感觉那儿已经很湿了,所以我很顺利地就进入了她的身体。我刚动弹了一下,就发现妻子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于是在她的鼓励下便试着加快了速度,不一会儿,她就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声。我知道妻子已经很兴奋了,但她还在竭力压抑着自己的呻吟,尽量不让别人听到。因为压抑,她的呻吟声在我听来并不是欢快,而是痛苦。 很快,我们就同时达到了高潮,就在我们快要把周遭的环境彻底忘掉时,突然听到了一声咳嗽。那声音是奶奶发出的,虽然很轻,但在我们听来却如一声响雷,顿时把我们吓得一动不敢动。我就这样趴在妻子的身上,屏住呼吸,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见奶奶不再咳嗽了,才慢慢地滑下妻子的身体,和她紧紧地挨着,老老实实地睡去了。 这次小小的惊吓,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妻子都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奖赏”我了。有时我憋得实在受不了,无论如何哀求她,她都无动于衷。为这种事,我也不好跟她生气,只得听她的。本来,这也怨不得她,谁让我家的住房这么紧张呢?她能不嫌弃跟了我,就已经不容易了,我还好意思怨她不“善解人意”吗? 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上海夫妻并不在少数。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克服这种困难的,但我的确在好长一段时间都被这个难题困扰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我们单位,不少刚结婚的年轻人也面临着我这样的困境。我曾在私下问过几个关系不错的哥们,有个哥们告诉我,他虽然家里情况和我差不多,但他妻子比较放得开,每天晚上他想做那个事时,她一般都不会拒绝。我奇怪地问,做那种事要发出很大响声的,他们难道不怕家里人听到?这哥们嘿嘿一笑,无所谓地说,怕什么,反正都是家里人,听见了也没关系。 我真羡慕这位哥们,羡慕他娶了这么位“放得开”的妻子。我的妻子张素芳要是能像他的妻子那样,该有多好呀?不过,转念一想,我又觉得张素芳之所以这样“放不开”,恰恰说明她是个很传统很正派的女人啊,一个男人能娶到这样的妻子,即使在性生活上不能得到满足,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吗?这样一想,我又觉得很宽慰。 还有个哥们,家里住房条件也很差:父母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同住在一间20来平方米的房子里。但这个家伙却非常幸运,他的父母和几个兄弟姐妹都是三班倒,有时轮到上夜班,赶巧了就赶到一块儿了,每个礼拜竟然能给他们夫妻空出两三个晚上来。想想看,整间房子里,除了他们小两口,别的人都去上夜班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那该是多么过瘾的一件事啊! 这样的幸运儿,毕竟太少,大多数的人都不得不像我这样,因为住房紧张而眼睁睁地断送掉自己的性福。我还不算最倒霉的,据说别的厂子里,还有这样一个倒霉蛋,他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家里每天不论白天还是夜里总有人在,他的老婆又像张素芳一样,是个“正派”的女人,不愿意和他在家人的眼皮子底下过性生活。慢慢地,他被憋得变态了。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偷偷溜进纺织厂,爬到房顶上看刚下班的女工洗澡,被纺织厂的保卫人员抓住后送到了派出所,最后据说以流氓罪被判了几年刑。 我曾把这个事例讲给张素芳听,谁知她听后竟不屑地说,真是变态、流氓,才判几年呀,太轻了,照我看,应该枪毙!我的原意是想让她明白,如果她再这么“正派”下去的话,过不了几年,我恐怕也会被压抑得变态,弄不好也会做出类似爬到女工澡堂的屋顶上偷看她们洗澡这样的事。